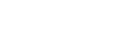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一页风云散,变幻了时空。这是历史的魅力,今天来讨论“司马光废除新法”的话题,或许有您所想了解的答案。
1085年,司马光正式复出,大举废除新法。司马光固然是一个性格偏执之人,但他通过制度设计和人才选拔,部分将自己的权力和偏执控制在安全范围内,维持了旧党内部健康的言论环境。那么,司马光为什么要废除新法?司马光废除新法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元丰八年(1085)五月,在洛阳赋闲了十五年之久的司马光正式复出,重回中枢,时年六十七岁。此前一年,司马光刚刚写下了《资治通鉴》的最后一行字。
这一年三月,宋神宗赵顼驾崩,这位变法皇帝启动的熙宁变法(王安石变法)也随之结束。更准确地说,是“被迫”结束,接位的宋哲宗赵煦年仅九岁,大宋的中央权力掌握在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氏手中,而这位从不掩饰对新法的反感的太皇太后,一掌权就着手大举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
废除新法需要人。在太皇太后手上,一大批在王安石变法中被边缘化、受到打压的“旧党”人物纷纷复出,如文彦博、吕公著、韩维、范纯仁、吕大防等人,而其中最被太皇太后所倚重的则是名满天下的司马光。
作为日后被指认的“元祐党人”之首,司马光此时在大宋旧党人物中,或者说“保守派”中是最有人望的一位。若欲全盘推翻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变法遗产,实现复辟,放眼大宋朝,没有人比作为“异论之宗主”的司马光更适合。
按照宋人笔记的说法,司马光还在洛阳时,“天下之人日冀其复用于朝”。用葛兆光先生在《洛阳与汴梁: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一文中的说法,司马光和洛阳的那一批旧党人物,仿佛一个现代所谓的“影子内阁”,很多人都期待着他们重新崛起执政。
大宋朝的百姓就是这么想的。宋神宗驾崩之初,司马光奔赴汴京奔丧,苦新法久矣的汴京百姓包围了司马光,不愿放这位众人心目中的救世主回洛阳,高呼“司马相公不要走,留下来辅弼新皇,给老百姓一条活路。”(“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
司马光一开始还是拒绝了来自太皇太后和朝野内外让他复出的巨大呼声,毕竟他已67岁高龄,身体已有中风的征兆,对朝堂上的政治斗争也心有余悸。但太皇太后认定了司马光是复辟的不二人选,下了好几次手诏责备说:“先帝新弃天下,天子冲幼,此何时,而君辞位耶?”
司马光的长兄司马旦也力劝弟弟复出,但最关键性的劝说可能来自和司马光同在洛阳靠边站的程颢:“除了司马相公您,朝野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废除现在的恶政。”说完这番话没多久,程颢就去世了。
君实不出,如苍生何。
司马光复出。
还在司马光正式复出前,他就为复辟解除了一个非常棘手的理论枷锁。朝中新党自知无法在权力上直接对抗太皇太后,就搬出了《论语》中“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的圣人语录,直指宋神宗尸骨未寒,新皇刚登基就急着废除新法是“不孝”。
司马光除了说了一番大道理反驳以外,还想出一个非常精彩的辩驳理由,直接在话术上驳倒了新党:“现在是太皇太后临朝,废除新法不是‘以子改父’,而是‘以母改子’,这又有什么可以顾虑的呢?”
好一个“以母改子”,太皇太后听完后如释重负,复辟之路再无大的障碍可言。
此后没隔多久,太皇太后就在司马光的推荐之下对中枢进行了全面改组,旧党官员纷纷复出,新党大员则渐渐被罢黜,从相反的方向重演了王安石变法时官员的“新旧更替”。
有了心底无私、一心为公的司马光,再加上号称“女中尧舜”的太皇太后保驾护航,看上去,复辟大业本应是一帆风顺,被变法中诸多弊端所累的大宋朝也终于否极泰来了。
但以老成持重著称的司马光却在形势一片大好之下,动作走形了。
复出之初,司马光还算是温和的复辟派,主张对新法进行必要的甄别,“便民益国者存之,病民伤国者悉去之”。也就是说,反对意识形态先行,对那些实际操作效果好的新法考虑予以保留。
事实上,宋哲宗的年号“元祐”,也是取了这个意思,按照宋人的权威说法,“元祐之政,谓元丰之法不便,即复嘉祐之法以救之。然不可尽变,大率新旧二法并用,贵其便于民也”。简单说就是,宋神宗的元丰新法有问题,现在找回宋仁宗时代的嘉祐之法补救,两者取长补短,则天下大治。
“新旧二法并用”,话是这么说,但没过多久,司马光就变得甚为偏激急躁,一如当年的王安石一样,自命真理在手,一意孤行,将“新法”和“旧法”绝对对立起来,凡是对方支持的我都要推翻,而且要立即执行,毫无妥协余地,将一切反对派视为“奸邪小人”,容不得任何反对意见。
司马光和王安石两人虽然政治主张完全相反,但从司马光最后十五个月的复辟历程来看,两人有一点是高度一致的:都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大公无私,为国为民,一旦认定自己的主张,就义无反顾,不顾个人荣辱利害的全力实现,其中既有罔顾现实情况的偏执盲信,也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执着。
很多人或许会很遗憾,为何人品高洁的司马光会在复出的这十五个月里,像王安石一样走向偏激,不知妥协与变通为何物。我想,可能会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司马光在洛阳坐了十五年的冷板凳,之前还经历了新党各种无所不用其极的政治打压,人非圣贤,你要说司马光复出后,对新党一点个人恩怨没有,一点也不会意气用事,可能也是过于神化司马光了,这和一心为公本身也不矛盾。
第二,司马光虽然官至宰相,但从他的政治履历来看,多在京师,少历外任,相对缺乏地方执政经验,即使在中央,担任的官职也以谏臣和侍讲为主,对政治实操中需要的妥协等“为官技能”缺乏感知力。
第三,和王安石一样,司马光在性格上也有学者的一面:较真、黑白分明、理想主义。司马光这种眼睛里容不下沙子的政治性格事实上更适合当台谏一类的官员,而当他全面主持中央政务时,缺乏妥协精神就成了他的性格缺陷。
第四,在他复出的十五个月中,司马光其实已自知时日无多,为了大宋朝日后的长治久安,他很可能想在剩下的时间里毕其功于一役,依靠自己的巨大威望,在短时间内迅速清除新法的遗毒,不想遗祸后世。这可能也可以被视作一种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吧。
虽然在复出后犯了一些王安石式的错误,但司马光终究有一点完胜了王安石——他身边的旧党同仁,在人品上比王安石提拔的“新党”强上许多。
当司马光意气用事走向极端时,他的这些旧党朋友们都站了出来,甚至不介意为新法说几句公道话,而不是像当年王安石变法时那样,新党诸人一个比一个偏激。谁能够更没有底线地推行新法,谁就能够飞黄腾达;谁能够提出更激进的变法方针,谁就能越级提拔。
比如说“免役法”,这是王安石最为重视的新法。他当然知道司马光上台后会“反攻倒算”,大举废除新法,所以一开始还强作镇定。元祐元年(1086)三月,当王安石得知免役法被废之后,终于把持不住,愕然失声道:“就连这个法也要废除吗?”(“亦罢至此乎?”)然后极其失落地说道:“此法终不可罢!我与先帝可是讨论了整整两年之久才决定推行,自问方方面面都考虑得很周全了”,说罢老泪纵横。
而“免役法”却又是司马光最为心心念念要废除的“恶法”。元祐元年正月,司马光大病一场,自知不久于世,但还是强撑着写信给朝廷说,当务之急莫过于废除免役法。言语之中,甚至透露出不废除则死不瞑目的决绝。
死不瞑目也是一种偏激,就是为了免役法的废除事宜,很多旧党朋友与司马光发生了激烈争论,甚至走向决裂。这些人未必也就是真的认为免役法有多么好,有异议一方面是觉得司马光的废除时间表过于峻急,主张慢慢推进;另一方面是反对来回折腾,既然木已成舟就边行边看。
作为旧党,苏轼、苏辙兄弟就对仓促废除免役法不以为然。苏辙认为,可以先认真总结一下新旧两法各自的优劣之处,和新党人物也应该和衷共济,一起边行边改,不必一上来就匆匆忙忙地废除差役。
苏轼激烈批评司马光说,“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苏轼当面向司马光指出,免役法和过去的差役法各有利弊,况且新法已执行了很久,老百姓已经习惯了,就算要废除也只能慢慢来。
司马光听后大发雷霆,苏轼便说:“当年韩琦大权在握,你作为谏官和他据理力争,韩公不高兴,你也不管不顾;现在你当了宰相,就不让我苏轼直抒胸臆了吗?”
司马光听后,马上笑着为自己的失态道歉,但依然固执己见。也难怪苏轼事后曾讽刺司马光为“司马牛”,说他的脾气和牛一样犟。“司马牛”和王安石的绰号“拗相公”倒是异曲同工,系出同源。
范纯仁也曾因为反对变法,而遭王安石贬逐,和司马光绝对算是亲密战友了。范纯仁作为老朋友劝说司马光,身为宰相应该“以延众论”,最忌谋从己出。他认为,新法中有一些可取的部分,不必因人废言,全盘否定,比如废除免役法,就可以慢慢来,先小规模试点,有了成效再全国推广,不必急于一时。
和苏轼一样,司马光对范纯仁的劝说也是置之不理,只当耳边风。范纯仁一声长叹:“奈何又一位拗相公。”
在废除青苗法的问题上,范纯仁曾和司马光起过一次更大的冲突。两人观点不同其实也没什么,这次苏轼、苏辙兄弟也支持司马光下重手废除青苗法的观点,问题是司马光那种咄咄逼人和动辄君子小人的说话方式,很难让人不想起王安石。
史书上是这样描述当时情景的。元祐元年八月,司马光得知范纯仁等人反对废除青苗钱之后,从病床上暴起,冒着重病冲进宫里,质问太皇太后:“不知是何奸邪劝陛下复行此事!”据说一旁的范纯仁当时吓得面如土色,连退数步,一句话也不敢说,青苗钱遂彻底罢去。
但对于司马光的执拗,方诚峰先生在《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一书中也做出了颇有说服力的“辩护”。方诚峰认为,从司马光复出时向太皇太后提供的“复杂多元”的官员名单中,可以看出司马光对未来大臣之间的异论纷争早有预期,并且他在事实上也接受了这样一种状态:在重要事务上,自己的主张“不过是多种意见中的一种”。方诚峰总结称,“可以确凿地认为,司马光主政期间,在多数重要政事上,都做到了各种意见的并存”。
在某种情况下,“妥协”和“坚持己见”并不矛盾。
也就是说,司马光表面上如王安石一般“司马牛”的背后,其实也有着一定的妥协和宽容,司马光选定的这些人,如苏轼、苏辙,如范纯仁,他们同司马光的“异论”,为元祐更化提供了珍贵的政治活力和弹性,恰恰保证了政治性格有缺陷的司马光不会滑向歧途和一言堂。
而这,难道不可以视作司马光的一种高超的政治设计吗?你甚至可以认为,司马光固然是一个偏执的人,但他通过制度设计和人才选拔,部分将自己的权力和偏执控制在安全范围内,维持了旧党内部健康的言论环境。
人有性格缺陷并不可怕,是凡人都或多或少有性格缺陷,但像司马光这样如苏轼所说的“至诚尽公,本不求人希和”,就真算得是道成肉身式的伟大了。
一个偏执者成就的伟大。
元祐元年九月一日,司马光去世,享年六十八岁。
此时,距离司马光的复出不过才十五个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司马光是累死的,是为了废除新法累死的。
复出前,司马光的身体状况已经相当不乐观,“目视昏近,齿牙全无,神识衰耗”,用李昌宪先生在《司马光评传》中的说法,“主持元祐更化,他是以衰残之年,羸弱之躯,任天下之责,挽狂澜于既倒,作最后的一搏”。
元祐元年正月,司马光就已病倒,卧病在床四个多月方重新入朝。但当时连走路都很困难,已无法行跪拜之礼。八月,司马光再次病倒,这次就再也没有起来。病中,司马光仍然惦记着废除新法的事,甚至有时不分昼夜地忙碌,有人劝他以诸葛亮“食少事烦”为戒,但司马光却答以死生有命。
临终前,司马光神智已经不清,喃喃自语,如说梦话,但所语“皆朝廷天下事”。家人整理遗物时,发现未及上奏的手稿八页,“皆论当事要务”。
除此以外,司马光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值钱的财产,史书上说“床箦萧然,唯枕间有《役书》一卷”,难怪老友吕公著写挽词说:“漏残余一榻,曾不为黄金。”
司马光死讯传开后,京城里上万人罢市去吊唁他,夹道哭送丧车离去,全国各地都有人来汴京购买司马光的画像,有的画工甚至因此致富。
太皇太后与十岁的宋哲宗亲赴司马光家中祭奠,赐以“文正”的谥号。据程应镠先生在《司马光新传》一书中所说,北宋一代,只有王曾、范仲淹三人获得过。
在司马光去世前约五个月,王安石也在金陵去世。
司马光虽然与新法似有不共戴天、除之而后快之怨念,但对王安石个人却充满着复杂的情感,对方去世时更展现了政治斗争之外的温情与善意。他在写给吕公著的书信中对王安石的人品和私德大加赞赏,“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他表示,“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主张朝廷对王安石“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正是听了司马光的建议,朝廷追赠王安石为太傅。
司马光去世后,他生前定下基调的“元祐更化”还延续了七年,直到元祐八年(1093),太皇太后去世,宋哲宗赵煦亲政。
尽管太皇太后高氏有“女中尧舜”的美誉,但在被压抑的少年赵煦看来,他一直生活在祖母垂帘的阴影之下,连带着将复辟的旧党人物也讨厌上了,认为他们只知逢迎祖母,不把自己这个皇帝当回事。赵煦回忆垂帘时,曾有一句充满怨念的话:“朕只能看朝中官员的臀部和背部。”(“朕只见臀背。”)
宋哲宗亲政后,新党重新上台,大宋朝廷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折腾。尽管只和司马光有过十五个月的交集,但或许出于对司马光当年“以母改子”宣言的不满,崇拜父亲的宋哲宗在以章惇为首的新党人物的影响之下,下诏剥夺了司马光去世时获得的一切哀荣,磨去碑文,砸毁碑身,甚至一度决定掘开司马光的墓,毁棺暴尸。
到了宋徽宗时代,自命为新党的蔡京拜相后,一度被司马光赏识的他将司马光以下共三百零九人扣上元祐奸党的帽子,将他们所谓罪行刻碑为记,立下著名的“元祐党人碑”。
司马光出生于1019年,如今已过千岁诞辰,他复出的这十五个月是他这一生最辉煌也最具争议的段落。
但他在复出时那些求快求全之失,一点也无损于他为国为民的伟大,我很喜欢苏东坡在祭文中的赞语“百岁一人,千载一时”,但还是觉得辛弃疾祭朱熹的那句话更适合在今时今日送给司马光:“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免责声明
本站部分内容来自于网络或者相关专家观点,本站发表仅供历史爱好者学习参考,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本文地址:/ysxl/lsqw/313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