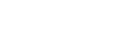最早体现沈德潜日隆的文化影响的,是他在1751年出任苏州紫阳书院山长一职。这座书院靠近苏州府学,由时任江苏巡抚张伯行(1652—1725)在1713年建成。在张伯行的赞助下,它起初是为了传播“正统”的程朱对于经典的注解(书院的名字既是指朱熹的老家,也与朱熹在福建武夷山主持过的书院同名)。在1750和1760年代沈德潜主持苏州紫阳书院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学院的指导方针开始发生变化,这所帝国最好的学校之一,成了汉学和考据学的中心。
鉴于沈德潜1750和1760年代的地位,他无疑是中间人的最佳人选,乾隆皇帝可以通过他影响更多的苏州学术精英,当时支持蓬勃发展的汉学的这些著名人物多已麇集紫阳书院。乾隆的头四次南巡,每一次沈德潜都得到了带领弟子迎驾的特权,乾隆皇帝也借此向紫阳书院及这位著名的山长赐诗。
在1751年迎驾中,沈德潜积极寻求乾隆皇帝对于紫阳书院的支持。
乾隆皇帝已准备好恩赐“白鹿遗规”匾额,也赋诗纪念:
德潜纵悬车,
乡教犹能振。
乞我四字额,
更无他语训。
白鹿有芳规,
气贵消鄙吝。
考虑到这时紫阳书院已是汉学的中心,乾隆皇帝提及白鹿洞书院,可能显得多少不合时宜,因为这使人想到一个人,就是朱熹这位程朱派理学的创建者,而汉学支持者却是要反对他。但乾隆皇帝认同朱熹,这暗示朱熹在制度史上而非学术史上的位置。朱熹毕竟已为书院的发展能得到皇帝的支持铺平了道路。可以说,朱熹所创立的制度先例以及白鹿洞书院,有效地使沈德潜与苏州紫阳书院一方,和以乾隆朝廷为另一方的日益发展的密切联系合法化了。
并非乾隆朝廷对于沈德潜及学生的所有讨好都是公开的。比如,南巡召试就是迎合那些处于苏州学术生活中心的人的更为普及和隐晦的手段。紫阳书院的学生在这些召试的中式者中占大多数,这是沈德潜至少是在苏州,在乾隆皇帝与学术精英间的文化迎合的博弈间,所起着关键性作用的进一步明证。
作为紫阳书院的山长,沈德潜自然要在学生中间宣扬自己的文学理论和鉴赏,包括培育一种对于宋以前文学——尤其是汉赋和盛唐律诗——的深层鉴赏。高信生认为,沈德潜对诗的感受受叶燮(1627—1703)、王士禛(1634—1711)影响,中心是促成(1)诗的“说教”和“格调”;(2)诗是“模效过去的杰作”的计量器;(3)琢磨不留痕迹的艺术品质。有学生记述说,沈德潜认为文学灵感之源在汉魏时期(220—265),唐代则是最高峰。仅在成为山长两年之后,沈德潜就编辑了他的七位最有才华学生的诗集《七子诗选》。他在这部诗选的序中(时间是在1753年8月),追述了“复古”的文学运动,这一运动在十六世纪达到了顶峰:
前弘治时(1488—1505),李献吉、何仲默结诗社,共得七人,称前七子。嘉靖时(1522—1566),王元美、李于鳞复结诗社,亦共得七人,称后七子。诗品虽异,指趣略同。
沈德潜提到明代“前七子”和“后七子”的共有倾向,包括“强调将已往杰作选集作为他们自己写作的范本并特别拒斥明代诗歌”。李梦阳(1473—1529)是“前七子”的领袖,坚定地表示“不读唐以后的任何作品”,特别提倡回归秦汉时期的文章类型和形式以及盛唐时的诗歌。沈德潜更是明确地将“南皮七子”也就是“建安七子”,视作文学灵感的一个共同来源:“岂偶然七子耶?抑慕南皮七子之风而兴起者耶?”更重要的是,沈德潜声称,他所选诗作的紫阳书院七名学生正高举着明朝复古思潮的火炬:
今吴地诗人复得七子,曰王子凤喈、吴子企晋、王子琴德、黄子芳亭、赵子升之、钱子晓徵、曹子来殷。此七子者数应偶符,然亦不可谓非风闻兴起者也。爰合钞而刻之,为《七子诗选》,请予为序。
吴中七子的文学倾向不仅与沈德潜自己的十六世纪复古运动审美联系有关,而且也与他主持下的紫阳书院普遍存在的汉学转向有关。江南的这七子,其中“三位是十八世纪最有影响的汉学家”,即钱大昕、王昶、王鸣盛,对于他们,我们马上会有更深入的了解。
除进一步强化皇权外,乾隆南巡期间举行的召试也迎合了沈德潜及学生的文学和学术偏好。召试要求考生用三种不同的形式完成皇帝指定的题目:赋、论、诗。更为重要的是,最初挑选参加召试的考生全部是看作诗的才华。这种形式在乾隆南巡中得以保持(只有一次例外)。
召试中钦定的赋的题目,常常是用来赞颂王朝的成就和巡幸活动的,而赋这种体裁本身正适合于此。例如,要求参加1751年浙江杭州召试的考生们写作的是“无逸”——这是强化民族—王朝问题所钟爱的题目(见第二章)。谢墉(1719—1795)是年轻的贡生,后来成了上书房师傅,他当时称颂皇朝“沛时巡之令,舒游豫之衷;惟循览乎方俗,勿晏处乎深宫”。谢墉的解释与乾隆皇帝对于无逸原则的意识形态改造相匹配,因此他能取中召试一等本不足为奇。第四章已指出,乾隆皇帝选择“观回人绳技”作为1762年江宁召试的赋的题目,这是乾隆皇帝大胆然而却是成功获得人们颂扬他近来辉煌军事征服的种种努力的一部分——这一次最好的颂扬来自程晋芳,他是扬州富裕盐商子弟,很有学识。
像谢墉、程晋芳一样,许多考生奉承乾隆皇帝。在朝廷看来,赋的引人之处,在于这种体裁合适,并且有作为一种夸张性颂扬以及表现皇帝洋洋自得的工具的历史传统。然而,在考场之外,一些地方士人暗暗流露出他们对于以赋这种体裁测试他们文学才能的矛盾心情,尽管他们显然能够从这样的活动中受益。这种矛盾心情,源自对于赋自身所固有的歧义理解,这也使得一些地方精英间接地影射一种可能性,即对于那些掌控政治权力的人要有更多的批判立场。
例如,1751年王昶作诗一首——《送张鸿勋栋、凌祖锡、褚晋升、钱晓徵、曹来殷赴金陵召试》。当时王昶是位二十六岁的举人,进入紫阳书院,成为沈德潜的弟子。他写这首诗是为了纪念五位同窗要离开苏州去参加乾隆首次南巡在江宁举行的召试。王昶的这首诗不应只作为饯行来读,而是他对于南巡召试,尤其是对考试辞赋的矛盾心情的细微表达:
柳外东风度翠旗,
恰宜献赋向銮舆。
璇宫方上升恒颂,
碧海频传赐复书。
建业莺声新雨后,
沧江颿影夕阳余。
自怜抱病风尘下,
遥望凌云重子虚。
王昶提到了崔骃(字亭伯,约30—92年)、司马相如(宇长卿,公元前177—公元前117年),这很难说是偶然。写这两个人反映出王昶敏锐地意识到赋不仅是文学修饰而且还有道德说教的潜在功能。崔骃,“璇宫方上升恒颂”,是东汉文学家,以劝谏闻名。康达维称司马相如是“汉代最著名的辞赋家”,是著名的讽谏范本《子虚赋》的作者(约公元前150年),这篇赋将两种对立意见并置,辞藻华丽。司马相如此赋的主人公子虚先生,被楚派往齐,一抵齐国,他通过将齐王不停的打猎与楚王更令人敬佩的出巡相对比,间接地批评齐王。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能够读出王昶诗作最后的所指,是请求他的同窗,要记住子虚先生的例子:对于贪求颂扬的统治者,能够保持批评(尽管是间接批评)的立场。
然而,在召试辞赋的应试中持有批评立场,不是件易事,谢墉、程晋芳的表现就是例证。赋毕竟不是一种纯粹进行说教的模式,而是“词藻装饰和劝说的结合”,这使作者有很大的灵活性,追求纯粹审美并更关注道义。然而,时移世易,审美掩蔽道义,赋演变成了一种广被蔑视的文学形式,人们认为它“道德的训诫混乱、歪曲”。甚至汉代文学辞赋家比如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他是辞赋乃一种修辞工具的最重要支持者”,最终也在后半生,“否认它是一种有效的说教手段”。
王昶与紫阳书院的同窗,对于文学史以及对赋这种体裁的批评,不可能无所闻知,因为他们全都精通汉代的文化和学术史。乾隆皇帝在南巡中使用赋似乎引发了一些质疑,至少是在王昶的心中,他没有与同窗一道参加1751年的召试。然而最终,这并没有阻止王昶及同窗参加南巡期间的召试。到1750年代末,王昶可能感受到的任何犹豫似乎已荡然无存。事实上,王昶自己与六位紫阳书院的同窗——钱大昕、褚寅亮(1715—1790)、曹仁虎、褚廷璋、吴省钦、徐曰琏——1751和1757年高中江苏的召试。此外,另两位同窗,也是吴中七子的成员——赵文哲、吴泰来——1762年江苏召试中分列第二名和第三名。
沈德潜及学生最终与乾隆朝廷达成和解,这不是发生在历史或文化的真空中,而是当时士人间内在紧张关系与对立的产物。在一个以对于唐诗与宋诗或是明朝复古派与袁宏道及公安派(下一章有更多的介绍)等等问题的优缺点进行激烈争辩为特点的学术蓬勃发展的时代,沈德潜及追随者,利用朝廷以实施他们自己的学术和文化规划。袁枚的观点显示出了士人间的这种激烈竞争,对于许多士人来说,这种竞争越发增强了赢得朝廷承认的重要和向往。
十八世纪晚期,袁枚已是当时“三大诗人”之一,其他两位是赵翼和蒋士铨。直到今天,袁、赵、蒋仍合称“乾隆三大家”。对我们当前的讨论更具重要性的是,袁枚也是沈德潜的头号反对者。用文学艺术家钱泳的话说:“沈归愚宗伯与袁简斋太史论诗,判若水火。宗伯专讲格律,太史专取性灵。”袁枚反对沈德潜陈腐的形式主义以及过分崇信诗歌的说教和政治功能,提倡美学的创新和个人的自我表达。因为这些诗歌理论和实践的不同,沈德潜及学生得到了皇帝的宠信,而袁枚却没有,尽管袁枚文学上声名籍甚,并在乾隆首次(1751)和第三次(1762)南巡中与圣驾有直接的接触。虽说袁枚从未直截了当地批驳沈德潜的诗歌,但他不满于这位前辈诗人的“卖弄学问和自满”姿态,猛烈批评沈德潜与朝廷的亲密关系以及那些从中获益之人:“当归愚极盛时,宗之者止吴门七子耳,不过一时借以成名,而随后旋即叛去。此外偶有依草附木之人,称说一二,人多鄙之。”
在南巡召试中,紫阳书院沈德潜的学生势不可挡的成功引人注目,但这并不是多令人惊讶的事。他们自己秉持汉学信条的文化倾向以及在王峻(1694—1751)、沈德潜等紫阳书院山长们的监管之下所得到的训练,毕竟让他们拥有与众不同的优势;最重要的是南巡召试,在很大程度上极重于赋以及赋这种体裁所要求的对于古代历史的精通。与赋有关的“词藻华丽的文体”和创作技巧,部分要归功于精通汉代的词汇学与语言学。大多数汉代辞赋家都是有学识的士人和诗人。十八世纪清代的汉学支持者,也接受了建立在博学基础上的古老和华丽的文学形式——袁枚会斥之为僵化的形式主义和卖弄学问。南巡召试中的文学题目使得一些有影响力的士人向乾隆朝廷靠拢,因此,乾隆朝廷有效地包容了1750年代发源于苏州的新的文化和学术趋势。钱大昕和王昶的经历尤其验证了来自苏州的汉家学和乾隆朝廷间,经由这些召试居间的迎合之举。
钱大昕,江苏嘉定人,出身于富裕的书香门第。从十二岁开始,人们就认为他大有前途,1742年十五岁时成为生员,1745年开始在吴城顾家做教席。作为苏州最著名家族一房的教席,钱大昕能够接触到大量图书,他开始熟悉新的考证学派方法——可能是受他的嘉定同乡王鸣盛的影响。 1749年,钱大昕和王鸣盛由江苏巡抚雅尔哈善招入紫阳书院,在那里他们结识了前辈学者,包括苏州汉学最德高望重的两位:惠栋、沈彤(1688—1752)。钱大昕发现身边都是情趣相投之人,包括同为“吴中七子”者——王鸣盛、王昶、曹仁虎、吴泰来、黄文莲、赵文哲——以及崔廷璋、崔寅亮兄弟。事实上,钱大昕此前已与这些年轻学者中的一些相过从。他已认识王鸣盛(他的同乡)和曹仁虎(他的表亲),当他和王鸣盛在1744年前往江宁参加乡试时,也可能结识了其他一些人。在苏州紫阳书院,这些才俊集中学习十三经(包括汉唐时的注疏),以及唐以前的语言和历史。如前所述,这一群体中除了两人(王鸣盛和黄文莲)外,全都参加南巡召试并被录取。
前文讨论王昶的饯行诗时指出过,钱大昕与紫阳书院四位同窗在1751年春参加了南巡的召试。钱大昕位居第二名,随后在1752年初被授予内阁中书,接着在1754年通过了殿试,成为盖博坚所说“十八世纪最著名的进士科”的一员。除钱大昕外,1754年的进士还有其他汉学家,有的投身于考证,有的最终在学术上有着广泛影响与声望。这些人包括王鸣盛、王昶、朱筠(1729—1781)、纪昀(1724—1805)——后二人在1770和1780年代《四库全书》的编纂中起着关键作用。
钱大昕在1750年代初抵达京城后,他的才能得到了京城大员的普遍赏识,这些人很快就将他的学术专长用于实际。他在与吴烺、褚寅亮一起研究梅文鼎的数学和天算理论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而吴、褚二人也是在1751年召试中取中,分列第三名和第四名。 1754年,礼部侍郎秦蕙田(1702—1764)邀请钱大昕协助编辑重要的著述《五礼通考》。两年后的1761年,工部尚书汪由敦任命时任翰林院学士的钱大昕,与纪昀一同编纂热河方志。正是由于这种身份,这两个人——现在人们广泛称之为“南钱北纪”——被任命跟随圣驾前往每年秋狝的所在地围场,为的是获取该地区的第一手材料。钱大昕在朝中任职,也受到有着同等情趣的何国宗(1712年进士,卒于1766年)等老一辈官员的极大赏识,何国宗是算学、天算以及历法的权威,不久之后于1755年率领一班官员去测量伊犁地区。钱大昕善算,其名声高于何国宗。当何国宗听到钱大昕在翰林院任职,就前去拜访,说:“今同馆诸公谈此道者鲜矣。”
钱大昕在朝时的学术活动很显然推动了清政权的利益。他在京时,也能够进行研究,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这一时期,钱大昕结识了戴震等著名学者,戴震于1754年抵京时就与钱大昕有往来。此外,钱大昕也常去南城琉璃厂书肆,搜罗了约二三百张拓片。在钱大昕自己看来,任职翰林院学士,能够很好地与自己学术兴趣的发展与追求相契合。
王昶也视追求学术与服务朝廷相得益彰。王昶是江苏北部青浦人,如上所述,人们认为他(与王鸣盛、钱大昕一道)是“十八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汉学家”。与钱大昕一样,王昶在1754年中进士后,在秦蕙田的全面指导下编纂《五礼通考》。然而,与钱大昕不同的是,王昶未能入翰林院清华之选,在北京停留了约一年后,最终还是回到了青浦老家,对于前景则多少有些不确知。1756年末,他应两淮盐运使卢见曾(1690—1768)的聘请,担任卢见曾族亲的老师,卢见曾也曾在秦蕙田《五礼通考》的编纂班子工作。
这一系列波折所带来的日益窘迫和失望,可能促使王昶参加了1757年的南巡召试,在苏州作为塾师毕竟不可能是一位三十一岁进士的终极抱负。无论怎样,在乾隆第二次南巡期间,王昶重申了他要将汉学用于经世。1757年江苏召试中的论的部分,要求试子们写作“经义制事异同论”。王昶的文章具有说服力:“古无经术、治术之分也。”王昶认为,在秦朝焚书后,“经生仅仅守其空文”,因此“经与事遂判然为二”。在王昶看来,到宋朝时“经义”“治事”依然为二,“终以虚文传世”,只有“经术与治术合大道,其不分同异也”。
王昶对于文本研究的强调以及他对胡瑗(993—1059)等宋代学者的不满,使得他在关于科举考试内容更广阔、持续性的争论中,表达了明确的立场,而这争论已经“在程朱‘宋学’的追随者和‘汉学’的赞成者间日益分化”。他对于“空文”“虚文”的贬斥,也与乾隆皇帝的关注有着共鸣,有着重合。乾隆皇帝自己不仅反复指出科举文章中的“虚文”问题,认为此已腐蚀了汉族士人和满洲旗人,而且“叹息人们过于关注科举文章,尽力鼓励关注更为实际的东西”。在1757年应试文章中,王昶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新的综合:一方面是严格的语言学,以考证方法为基础,旨在复原他及其他汉学家所认为的被汉代以来所误读的经文原意;另一方面则是关注实政。在这一点上,王昶的文章,反映出在汉学的倡导者和乾隆朝廷之间的一种渐进却是日益增长的利益迎合。王昶在1757年江南召试中位居一等,这进一步支持了这种看法。
王昶同钱大昕一样,发现有大量的机会去实践他将考证与实政重新结合的认识。1758—1768年在北京的十年间,他协助编纂了一些官方著作,这些著作对于伊犁河谷和塔里木盆地的治理至关重要,包括多语言的词典《西域同文志》(1766)以及《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
王昶和钱大昕值得特别关注,是因为他们在苏州汉学中的卓越地位以及他们与沈德潜的密切关系,而他们的发展轨迹也合乎一个更宽泛的笼络士人模式。许多人包括王昶和钱大昕,最初他们的博学及文学才华得到认可与称赞,如同南巡召试中所证明的那样,然而,一旦为官,他们就会受到邀请(以及被要求)将他们的广博知识和学术专长服务于家产制政权。作为关于日益扩大的清帝国边疆的官方编纂工程的贡献者,王昶和钱大昕都深深卷入了文朵莲所说的“创造国家文本空间的学术活动”和“为帝国做解说”中,他们因此成了清朝民族—王朝统治的积极代理人。

免责声明
本站部分内容来自于网络或者相关专家观点,本站发表仅供历史爱好者学习参考,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本文地址:/bjwh/zdgc/1898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