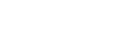在1882年,埃及看似正走在成为一个繁荣的现代国家的道路上。其进步主要归功于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及其继承人的野心和力量。在过去的60年中,他们已将这一国家作为私人地产运作。他们鼓励对灌溉、铁路、造船、棉花种植园、中小学和大学的投资。埃及2/5的耕地为棉花种植地。其所种植的棉花大部分出口到英国。它是埃及的主要贸易伙伴。英国和法国为重建埃及支付资金。1880年,其总债务超过一亿英镑。对于一个年出口总额平均为1300万英镑的国家来说,这一数额甚巨。
尽管总督伊斯梅尔(Ismail)将他在苏伊士运河44%的股权出售给英国以换取400万英镑,到了1875年,埃及依然陷入破产的漩涡。大国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让她振作起来:1876年,一个国际委员会对政府进行委任统治,执行财务紧缩政策。三年后,新总督陶菲克(Tawfiq)被说服接受英法对其财政的控制。这两个国家控制了埃及的海关、邮局、电报、铁路、港口甚至是博物馆。埃及主权逐渐受到了侵蚀,外国人也渐渐控制了其政府。外国人对埃及主权的侵蚀肯定会招致民族主义者的反对。这首先导致了1881年2月由没有领受到薪水的军官所进行的抗议。这一抗议行为是由阿拉比(Urabi)帕夏所领导的。在接下来的9月,他发动政变(coup d'état),自己担任战争部长并完全控制军队。阿拉比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将他自己所来自的小农阶层与受过良好教育的地主和官员联合起来。资本主义农业正在蚕食小农们的土地,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源于曾在埃及购买土地的外国人。艾芬迪亚(effendiya)也因外国人侵入政府职位而受到警告。埃及国内自然也有关于埃及将被外国直接接管的恐惧。1881年春季和初夏,法国人正在为其吞并突尼斯做收尾工作。
人民民族运动在埃及出现。随之而来的是,其政府可能不会听从外国官员的指令,也可能不会按照英法银行家的意思办事。这一点使得英国和法国政府措手不及。1881年10月,他们开出了每当无形帝国各地出现问题时的一般解药,将两艘铁甲舰送到了亚历山大里亚。令人烦恼的是,这些并没有改变埃及人的主意。
英国政府进退两难。自从两年前,格莱斯顿内阁的工作就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那时,他们反对保守党不道德的冒险主义,并推行一种基于国际合作的亚太外交政策。如果要使得这一点在埃及发挥作用,英国和法国必须共同经营,并取得欧洲其他国家的支持。他们试图制定一个旨在恢复现状的、共同的盎格鲁——法国(Anglo-French)政策。但是,在埃及发生的事件使得这一希望化作了泡影。
1882年6月11日,一个埃及驴车夫和一个马耳他人之间的票价之争引发了一场亚历山大里亚的骚乱,其中有近50名外国人被杀害,他们的财产则遭到掠夺。这被认为是埃及走向无政府主义的第一步,也震动了伦敦和巴黎的货币市场。恐慌的法国投资者开始抛售埃及股票。商界人士当中的不安情绪表现在《经济学家》当中。该杂志于6月17日预测说,如果不采取措施制止埃及的混乱的话,“(我们)即将蒙受巨大的损失,而企业也将遭受巨大的干扰”。议会当中,议员们中充斥着愤怒的情绪,并要求采取行动。“我们下议院中关于埃及的立场是非常沙文主义的,”内阁成员查尔斯·迪尔克爵士(Sir Charles Dilke)写道,“他们很想杀人。但他们不知道该杀谁。”如果要进行杀戮,格莱斯顿希望法国会伸出援手,但是在7月1日,法国议会投票果断反对武装干涉。
英国现在独自面对阿拉比的进一步挑衅。在其部队在亚历山大里亚恢复秩序之后,他下令运用现代克虏伯大炮加强对港口的防御。现在,一支实实在在的英国舰队正横在道路之上。7月3日,其指挥官海军上将比彻姆·西摩(Beauchamp Seymour)要求卸下新的炮组。阿拉比拒绝了这一要求。八天后,内阁批准向炮兵阵地进行轰击。7月13日,登陆的水兵和海军陆战队进入亚历山大里亚。在阿拉比的军队离开后,此地的法律和秩序已经崩溃。
为了给英军攻击防守工事一事辩解,格莱斯顿宣称:“埃及正处于爆发军事暴乱的边缘,此地没有任何法律可言。”因此,他的政府准备派遣远征军,以恢复秩序并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在8月的时候,两支军队在沃尔斯利(Wolseley)的指挥下在埃及会师。它们分别是一支24000多人的英国部队和另一支7000多人的印度部队。军舰在不受阻力的情况下占领了运河。当月18日,英国军队在伊斯梅利亚(Ismail)登陆。四个星期后,英国军队攻陷了阿拉比在泰勒凯比尔(Tel-el-Kebir,又称al-Tallal-Kabir)所建立的、有防御工事的营地。这为成功进入开罗铺平了道路。阿拉比被俘并接受了军事法庭的审判。之后,他又被流放到锡兰。
发生的事情令格莱斯顿政府十分尴尬,并争辩自己除去防止埃及自我毁灭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在这样做之后,英国会以同样高尚的利他主义精神来监督埃及的复兴。这将会由一组英国官员所完成。他们将会在伊夫林·巴林(Evelyn Baring)爵士(后来成为克罗默勋爵)的指导下监督国家行政。与此同时,埃及军队将在一系列英国高级官员的手下重新展现活力,并由陆战队军士辅助操练。在成立之初,据说这种控制体系是一项临时措施,直到埃及不再需要监护为止。
在埃及,英国人创造的是一个帝国的混血儿。它既不是殖民地,也不是一个正式的保护国。对外,它仍是一个由总督统治的独立国家。按照纯粹的法律意义上来说,其领主是土耳其苏丹。现实是,自1882年之后,埃及的国家权力掌握在英国官员所组成的高级文官手中。其首要任务是恢复该国的偿还能力。克罗默和米尔纳两个人后来写作了大量的书籍,以解释英国到埃及的使命,并认定已经完成的事务能够促进埃及人的幸福。
然而,这种将占领埃及认定为对该国人民服务的正统观点受到了挑战。挑战者是那些认定1882年英埃战争是一些投资者强加给政府的人。前保守党议员和锡兰州州长威廉·格里高利(William Gregory)爵士争辩说:“我们是唯一一个同情尼罗河河谷不幸的农民的诚实民族。但我们被迫成了黑人的驱赶者。为了债券持有人的利益,我们被迫成为带鞭子的管理者,从这些可怜的穷人手中拿走最后的皮阿斯特(piastre)。”不信任任何金融家阴谋的托利党乡绅威尔弗里德·斯卡文·布朗特(Wilfrid Scawen Blunt)履行并扩大了这一原则的实施范围。他的这一行为与安东尼特·罗洛普所写的《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The Way We Live Now)当中固执和不诚实的奥古斯塔斯·梅尔莫特的所作所为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有趣的是,传统的保守党和左翼极端分子都认定,19世纪80和90年代新帝国主义的表现受到了资本的秘密影响。
在埃及,英国的占领激发了深沉的愤慨。克罗默一边公开吹嘘小农感谢英国政府的公正,一边又在1902年向帝国国防委员会(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se)承认,如果法国或俄罗斯入侵他们的国家,埃及人几乎不会保持忠诚。1914到1915年冬季,德国最高统帅部相信,进攻埃及会立即触发反英起义。这样的结论并不令人惊讶。英国力量已进入埃及来镇压民族运动,而且,大山战役之后的情感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烟消云散。顺便提一句,小农出身的士兵曾在此地固执地作战。在所有埃及人当中,特别是受过教育的阶层当中,民族主义仍然是一个强大的情感力量。这些受过教育的人发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公务员、司法和军队的最高级别之外,因而比起普通人感到更为不平。尽管英国建立了一张充满活力和高素质的警察情报网络,民族主义风潮继续在八九十年代盛行,而陶菲克的继任者阿巴斯二世则在暗中煽动。1900年1月,驻扎在喀土穆的埃及军官受到英国在南非遭到击败和俄罗斯正在向印度挺进的谣言鼓舞,鼓励他们的苏丹土著士兵(askaris)发动兵变,希望这一兵变可能促使英国人被驱逐出埃及。
那么,还有什么能够让英国人留在埃及呢?能够自由通过苏伊士运河似乎成了迫使其留在此地的理由。在1881年使用运河的2727艘舰船当中,有2250艘为英国船。然而,无论何时,阿拉比都没有做出过表明他可能会妨碍运河运行的决定。1914年8月战争爆发之际,正是英国在埃及的统治结束了运河作为国际水道的地位。当然,在1882年,人们还无法预测阿拉比未来的行动。最重要的是,如果英国无所作为,另一个力量将会介入。
最后,正如在许多无形帝国遭到破坏的地区一样,为了占有这一国家,英国人唯一的选择是在当地建立有形帝国。而在这一情形下,他们采取了极其迅速地占领此地的方式。更何况,无论英国人是否在此地采取动作,他们都无法获知法国代表的态度是否会改变,以及大多数人是否会赞成干预。随后国际形势的发展为这一论点提供了论据。1885年英法殖民主义之间猜忌情绪的滋长,1892年的法俄同盟以及随之而来的、地中海可能会成为法国帝国主义梦想中“法国内湖(le lac franais)”的前景,都令英国人判定,1882年的决定是合理的,排除了任何从埃及撤军的可能。19世纪80年代末,土耳其不再是一个阻止俄罗斯海军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可靠力量。这一点的逐渐显现为掌控埃及进一步提供了证据。在英国的国际影响方面,埃及所花费的成本很高。为了获得对她的立场的支持,英国被迫做出妥协,并向德国和法国让步。如果情况有所不同的话,她可能会拒绝。
****
拥有埃及也给英国带来了其他责任。在逐渐征服和平定战争60年后,苏丹仍然是一个动荡的地区,此地的埃及权威仍旧脆弱。四万名士兵和官员努力压制混乱,并为埃及总督的统治收集足够的税费。当时,埃及政府一直在从事抑制奴隶交易的工作。这一责任主要是由外国总督所承担的,其中包括著名的查尔斯·戈登(Charles Gordon)将军。
1881年,埃及当局面临一个由穆罕默德·艾哈迈德(Muhammad Ahmad)所领导的新叛乱。他是一个37岁的救世主般的神圣之人,自称为马赫迪。作为一个穆罕默德所选择的仆人,他的任务是净化伊斯兰教,并惩罚那些信仰已经失效或受到污染的人。凭借简单的虔诚、强大的信念和精神重生,他赢得了成千上万的、称为安萨尔(辅士)的信徒。他攻击并占领了欧贝德镇(El Obeid)。在克罗默的许可下,一支由威廉·希克斯上校(Colonel William Hicks)所指挥的装备精良的埃及军队来到南部镇压起义。这一军队在沙漠里徒劳无功,而希克斯则于1883年11月在赤坎(Shaykan)遭到埋伏。他的军队被击溃,而其步枪、机枪和火炮则被缴获。1883到1884年的冬天,马赫迪的信徒之一,奥斯曼·迪格那(Uthman Diqna)开始在红海港口萨瓦金(Suakin)附近建立一个新的战线,并攻击当地的埃及驻军。
显然,埃及军队不能应付,更别提抑制马赫迪运动。在苏丹,埃及的统治正在崩溃。内阁在1884年1月同意将所有埃及驻军和人员疏散,而不是在沙漠战争上浪费财富和人力以维持其统治。从此地撤出帝国力量与帝国征服一样复杂和令人烦恼。1884年2月赶往萨瓦金的部队很快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与奥斯曼·戴安那之间的力量对决,并因此被迫发动一系列小规模的战争,以维护英国声誉。通过在埃尔·塔布(El Teb)和塔马伊(Tamai)战争的胜利,英国的声誉得以保存。在这里,英国士兵首次惴惴不安地领教了安萨尔们(他们常常被称为托钵僧)的坚韧和勇气。
查尔斯·戈登(外号“中国人”)将军全面监督从苏丹撤军的行动。这是一个有争议的任命,表面上是因为他以前的本土经验,但实际上是由媒体推动的。戈登已经是一个受欢迎的英雄,他的勇敢和强烈的传教士般的热情必将吸引维多利亚时期的公众。戈登固执并坚信自己的魅力。他将自己视为天意的传达人,而且正如格莱斯顿一样,认定他的决定对上帝负责。他还拥有一种鼓励非欧洲士兵的特有天赋:在19世纪60年代,他代表中国皇帝指挥“常胜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19世纪70年代,他领导埃及军队对抗苏丹的奴隶贩子。虽然他拥有基督教热情,且几乎不会说任何阿拉伯语,但他相信他能够得到苏丹人的支持。他在2月抵达喀土穆时受到了热情接待,因而他们对他的忠诚得到了证实。但他不理解的是这样的一种热情来自于市民们认为他有权召集英国士兵。在萨瓦金的事件已经表明,英国士兵能打败马赫迪的安萨尔。戈登没有过分担心马赫迪。他误认为这场运动没有多少群众基础,不可能取得更大的进展。因此他放弃了其所接受的撤离苏丹的命令,而是准备保卫喀土穆以抵御马赫迪。
戈登凭一己之力改变政府政策。在喀土穆,他发表了一系列高度情绪化的,对公众良心具有强大感召力的吁请。他呼吁他的同胞承担文明的负担,并从他所认为的黑暗势力手中拯救苏丹。他的恳求和困境吸引了公众的想象力;他是一个在偏僻的土地上的、四面楚歌的战士,认定基督徒的责任和服务主要是人文主义的,然后才是私利。舆论转向支持戈登。8月初,舆论迫使不情愿的政府派军队去救他。
戈登的地位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自5月以来,马赫迪军队已经在喀土穆附近聚集,这使得暴民无法疏散。马赫迪军队中的主力军于9月聚集在该市。一个月后,马赫迪下达了攻城命令。在此期间,由沃尔斯利指挥的10500多名远征军集合起来,并开始谨慎推进到了尼罗河。媒体和公众将战争看作一场竞赛,但因为得知沙漠已经吞噬了希克斯的军队,沃尔斯利一如既往地小心推进。
1885年1月上旬,军队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库尔蒂(Kurti)。沙漠军团将从那里跨越拜尤达沙漠(Bayuda desert)抵达阿尔·马塔马(al Matamma)。在这里,一支象征性的支队将踏上从喀土穆派出的三艘蒸汽轮船。在戈登的指令下,它将运送穿着传统红色夹克的而不是卡其色夹克的人。这是为了说服苏丹,英国人真的已经到了。马赫迪意识到了增援部队正在靠近,命令他的将军们在阿布科里(Abu Klea,又名Abu Tulayh)的水井处拦截沙漠军团。
随之而来的是一场经典的帝国战争。英国军队刚刚超过1000人,许多骑兵骑着骆驼。情报部门告诉他们不用期待会有严重的阻力,而这些骑兵自己也不知道对手的数量和所做出的努力。他们第一次看到敌人,是隐藏的峡谷上飘扬的绿色、红色和黑色的旗帜,上面书写有《古兰经》的文本。
突然间,矛兵骑着马、扛着所有的旗帜,以一种迅猛的速度向我们冲过来。敌人以非常快的速度以及极为密集的数量冲向我们的方阵。(与此同时)他们也保持着主要的次序。
散兵跑回到方阵里面,而方阵也开放一个口子来接受他们。正是通过这一间隙,一些托钵僧蜂拥而出。直到最后一刻,步兵也无法辨明他们的攻击者。在方阵裂开的地方,有“一大群叫喊的人和骆驼——他们或是活着,或是已经死了,或是奄奄一息”。承担反败为胜任务的是方阵中没有遭受攻击一侧的士兵。他们多留了一个心眼,调转方向并向混乱的群众齐射。此后,裂缝合拢,袭击者则被击退。这一切都是在不到20分钟之内结束的,但伤亡数量甚巨,所有参与的士兵都为安萨尔的凶猛大胆而感到震惊。
死者中有布鲁斯的弗雷德里克·本拿比(Frederick Burnaby)上校。蒂索(Tissot)为其创作的著名画像将他表现为一副优雅且不顾一切、满不在乎的样子。而这些品质也是一个完美英国军官的标志。毫无疑问,他肯定赞同那些同事们的观点。他们在战争结束后表示,如果在不知道结果的情况下已经被杀了,这是很糟糕的。在近一年前,本拿比已经参与了萨瓦金的战斗。那时,有关他向托钵僧“乱射”、并将他们当成是鹧鸪一样的新闻报道令左翼自由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感到震惊。本拿比是议会保守党的候选人一事可能更加增加了他们的愤怒。
阿布科里的战争引起了帝国缪斯们的创作热情。在《生命的火炬》(Vitaï Lampada)当中,亨利·纽波特爵士(Sir Henry Newbolt)将战场视作公立学校所培养美德的试验场:
沙漠中的砂子是浸透了的红色,
是被方阵中士兵的鲜血染红的。
格林枪哑火,上校死去,
团中士兵被尘土和烟雾迷住双眼。
死亡之河溢上河岸,
英格兰很远,光荣不过是个名称。
但,一个男学生重振了各级的旗鼓。
“加油!加油!开始比赛!”
吉卜林转向失败者。在他的“毛毛(Fuzzy Wuzzy)“(因为哈顿多阿Hadanduwa部落特有的浓密发型,士兵们给托钵僧起的外号)一诗当中,他假想出了伦敦士兵向他们不计后果的勇气致敬的一套颂词:
在我们射击的时候,他冲进烟雾当中;
仅在一念之间,他已经在劈砍我们的脑袋;
他看起来已经死去,这往往是假装的。
他是一流的人物,他对人和蔼可亲,他是个温顺的人!
他是宴会上的印度橡胶(injia-rubber)白痴,
他是唯一不在乎
英国步兵团的人!
所以,这首诗是献给你的,毛毛,在你苏丹的老家,
你是可怜而愚昧的野蛮人,但也是一流的战斗员;
所以,这首诗是献给你的,毛毛,顶着你那一头干草堆式的头发——
你这高大、黝黑、雀跃的乞丐——因为你击溃了一个英国的方阵!
在阿布科里之后,沙漠军团两天后移师到埃尔·马塔马(al Matamma)。托钵僧进一步的攻击迫使指挥官采取防御措施。只有到了1月24日,轮船才驶向喀土穆。听说丈夫已经在阿布科里战死,喀土穆城内妇女们的哭喊声此起彼伏。此时,这座城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战争的消息促使马赫迪冒着风险向该城进攻。突击成功了。1月28日,随着轮船向喀土穆迫近,很明显的是,它已经陷落。
戈登最后的命运如何?钦佩他的坚定和勇气的马赫迪起初试图活捉他。40年后,目击其最后时刻的安萨尔证明他是在战斗中死去的。其中一个目击者声称,他用左轮手枪攻击了几名对手之后开枪自杀。这一口述证实了在喀土穆被俘的卡尔·诺伊费尔德(Karl Neufeld)的记述。他认定,战斗中的戈登显示出了“超人的力量”。2月,信息沿着这些线路传达到沃尔斯利的情报部门,但它与此后来自不可靠来源的更具戏剧性的故事发生了冲突。按照这些描述,戈登空着双手且衣着整齐,孤傲地站在其喀土穆居所的阶梯上,轻蔑地盯着数量众多的安萨尔。他轻蔑地掉头离开,并被刺杀身亡。
这个版本的戈登死亡故事是由情报部门的雷金纳德·温盖特(Reginald Wingate)爵士所发布的。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基督教英雄唯一恰当的结局。他知道戈登的“殉难”会激发他的同胞们重新占领苏丹以作为报复。因此,这一熟悉的形象出现了:戈登面对他的敌人,并为了文明事业最终做出自我牺牲。这就是英国人如何看待他的死亡的。“文明遭受了严重的损失。”1885年2月7日,正当沮丧和愤怒的浪潮席卷全国之时,《观察家》如是宣布。格拉斯顿成了众矢之的,处处受到责难。他别无选择,只能承诺发动全面战役收复喀土穆和制裁苏丹。
3月,越过阿富汗边境的俄罗斯的入侵导致了一场总军事动员,格拉斯顿就此得以解脱。军队从苏丹撤退,并运往印度,只留下驻守萨瓦金的一支守备军。6月,马赫迪死了,死因可能是因为斑疹伤寒。苏丹的管理权落入了(继任)哈里发阿卜杜拉·本·穆罕默德(Abdullah bin Muhammad)的手中。1889年以后,他好战的伊斯兰国家就没有对埃及造成任何威胁,那时,他入侵的部队在托斯基战役(Battle of Toski,又名Tushki)中溃败了。
****
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政治家和军事策略家担心,敌人能够人为切断尼罗河。其结果是埃及的农业将遭到毁灭,而国家则将覆灭。人们一致认为,阻断尼罗河远远超越了哈里发统治下苏丹的能力,但欧洲工程师可以做到这一点。这是法国水文学家维克多·普朗普特(Victor Prompt)的观点。他于1893年1月发表专业论文,描述了如何在尼罗河上游建造一个大坝来有效地切断埃及的生命线。事实上,这一计划不可行,但其可能性令法国殖民大臣提阿非罗·德尔卡塞(Théophile Delcassé)着迷。普朗普特的方案以及法国官员对它的兴趣造成了英国方面的惊愕。一段时间以来,他们一直努力保证国际上的认可,以垄断对尼罗河流域的控制权。他们也同时尝试控制白尼罗河源头维多利亚湖的北岸。
1888到1898年,对于由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政府以及比利时利奥波德二世国王所参与的一盘大棋局来说,尼罗河的源头各国都在争夺。此时,尼罗河源头实际上的主人是称为刚果自由邦的私有产业。
作为埃及实质上的统治者,英国声称自己继承了从该国一直延伸到维多利亚湖的尼罗河河谷的历史合法权益,并急于保护自己的海岸。英国传教士已经侵入了现在被称为乌干达的这一地区。1888年,他们的赞助商之一、白手起家的苏格兰商人威廉·麦金农(William Mackinnon)爵士成立了大英帝国东非公司(British Imperial East Africa Company)。按照政府所颁布的特许状,这家公司有权发展贸易和扩大英国的影响力。迄今为止,东非的主导权掌握在德国人的手中。它的利益是由精力充沛的探险家卡尔·彼得斯(Carl Peters)所争取到的。从1884到1885年为止,他与达累斯萨拉姆(Dares-Salaam)腹地的本地统治者缔结了一系列条约,为德国制定统治下东非(坦噶尼喀)的法律提供了基础。由于热衷获得与海外领地相关的声望,意大利人在埃塞俄比亚和非洲之角集中精力。在法国方面,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因为她的野心集中在西撒哈拉,法国处于这场较量的边缘,尽管在1885年,她已经得到了法属刚果,即刚果河北岸的一个小殖民地。那条河的南岸及其广阔的内陆流域是利奥波德二世的个人财产。他的所有权是欧洲各国在1885年柏林会议上妥协的结果。但人们无法获知的是,他所成立的、利用该地区的公司是否将蓬勃发展。如果失败了,那么法国希望介入。
1888年,争夺中部非洲的较量开始第一次发动。每一个玩家都非常关心救援爱德华·施尼策尔(Edward Schnitzer)的行动。这位西里西亚的犹太人在作为苏丹总督手下的一名地方总督的时候接受了埃明帕夏(Emin Pasha)的称号。喀土穆沦陷后,他带领其剩余的手下和军队向南到达赤道,在那里他陷入了困境。麦金农和彼得斯计划了武装探险,希望以人道主义的名义救出他。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尼罗河源头附近插上自己国家的国旗。但是,麦金农和彼得斯被亨利·斯坦利(Henry Stanley)爵士所击败。这位出身威尔士济贫院的男孩先后担任过战地记者、探险家,也是利文斯敦的发现者。1885年,他担任了刚果自由邦的官员。斯坦利带回了埃明。而且,通过他在赤道短暂的停留,宣示了他的皇家主人对该地区的主权。
这一事件令索尔兹伯里勋爵政府感到震惊,旋即采取行动。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手段的确定,它与意大利、德国和利奥波德二世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至少在字面上,这些协议肯定了英国在尼罗河流域的至上地位。1890年的英德协定肯定了英国对乌干达和现在的肯尼亚的主权,也肯定了德国对坦噶尼喀的主权。这一安排得以实现的前提是,英国愿意用北海上的赫尔果兰(Heligoland)岛交换桑给巴尔(Zanzibar)。下一步在于与意大利达成一致。自1885年以来,英国一直在鼓励她在埃塞俄比亚的野心,甚至把埃及的红海港口马萨瓦(Massawa)送给她,以便在厄立特里亚(Eritrea)的行动。出于感激,意大利人承诺在1891年不染指尼罗河河谷。三年后,罗斯伯里勋爵(Lord Rosebury)的自由党政府经过相当大的内部辩论,同意宣布在乌干达建立一个保护国。在那里,大英帝国东非公司金融崩溃与部落战争蔓延同时出现。不久之后,利奥波德国王保证不把他财产的边界推向尼罗河上游。因此,到了1894年,国家间的较量是有利于英国的。在这个阶段,法国成了游戏的新玩家。
法国向白尼罗河畔的领土出价旨在推翻埃及新的政治秩序。一旦明确了英国不打算在可预见的未来放弃她的地位,法国就变得越来越愤怒和怨恨。对英国强大的敌意主要是由右翼极端民族主义政客、官员、士兵和报纸编辑所游说策划的。他们声称,她贪婪的邻居正在故意欺骗法国。法国在埃及恢复合法影响力的唯一途径在尼罗河上游某处对英国发动积极的挑战。如果成功的话,这将迫使英国撤离埃及或承认那里的权力分享状况。这样的结果将大大提高法国的国际威望,地中海的权力平衡也将向她倾斜。在法国政治圈里,不是每个人都相信这一点;有一派观点认为,如果英国被迫离开埃及,整个近东和中东就将是不稳定的。这将损害法国的利益。
无论如何,政府、军队和殖民政府中的反英派决心先下手为强。1894年底,上乌邦吉官员维克多·利奥塔德(Victor Liotard)奉命向尼罗河上游进发,但部门领导的变更导致他的命令被撤销。1895年的夏天,发动第二次远征的计划正在酝酿中。让-巴普蒂斯特·马尔尚(Jean-Baptiste Marchand)上尉将担任指挥官。他拥有坚定的信念和丰富的殖民地经验。在过去的十年中,他一直忙于在西撒哈拉竖立三色旗,而且经常无视巴黎的意愿。马尔尚是最适合这个工作的人。1897年3月,他带领着163名军官和土著士兵从加蓬出发,履行命令,与任何他在尼罗河上游所遇到的人洽谈“严肃的联盟和无可争议的份额(alliances sérieuses et des titres indiscutables)”。他和他的赞助者知道,他所从事的事情是一场赌博。而且后者中的一些能够明显地与詹姆森突袭相比较。
马尔尚及其军队于1898年7月抵达尼罗河上游岸边的法绍达(Fashoda,又名Kokok)。在这一史诗般的旅程中,他有时会骑一辆带有坚实轮子的自行车。现在这辆自行车保存在博物馆的圣西尔军校。当他骑着自行车穿越撒哈拉南部,法国索马里兰的总督正在秘密和埃塞俄比亚皇帝孟尼利克二世(Menelik II)联系,为其提供保护和友谊。
英国政府之所以会批准在1896年3月发动第一阶段的苏丹夺回行动,法国可能会入侵一个名义上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地区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在于,孟尼利克最近在阿杜瓦(Aduwa)击败了意大利军队,尼罗河上游流域的力量平衡遭到了改变,严重损害了欧洲的声望。赫伯特·基钦纳爵士指挥下的埃及和苏丹军队以埃及之名向南方的喀土穆进发。出身新教的乌尔斯特(Ulster)的基钦纳是一个具备相当能量的士兵。其中大部分能量都用于其职业生涯的发展。他是一个热情的帝国主义者,相信他是以文明之名在苏丹发动战争。这一考虑并没有阻止他极端残酷地对待敌人。
不可避免的是,基钦纳的战争是一个缓慢、渐进的向尼罗河下游的推进过程。它也证明了在站线后设立单线的铁轨是如何有逻辑上的必要。这令许多随军的战地记者感到兴奋,并向公众发表热情洋溢的报告。战争的新闻版本将征服者的现代技术与对手的野蛮相对比,不断强调英国的崇高动机。对苏丹的入侵既是一次为了发展文明的十字军东征,也是为戈登之死复仇的行动。
1897到1898年冬季,公众对战争的兴趣日益增加。此时,在基钦纳的要求下,更多的英国部队被派往准备与哈里发主力军的最后决战。这一军队人数被认为有60000多人。政府预计将会获得一场胜利,并已经在考虑苏丹未来的政治解决方案。索尔兹伯里放下其有关负担统治一个广阔且无收益的省的顾虑,并接受英国占领整个苏丹是不可避免的这一事实。需要当心的是马尔尚。1897年底,在索尔兹伯里的允许下,英军向马尔尚远征军发动了攻击。此时,J.R.L.麦克唐纳(J.R.L.Macdonald)少校奉命率领苏丹的土著士兵沿着从乌干达发源的白尼罗河向北行进。他的目的是防止马尔尚所部和法国另一支军队会合。但他错误地估计了另一支军队前进的方向,认为这支法军会从埃塞俄比亚行进到尼罗河边。马尔尚和麦克唐纳之间并没有发生冲突;在出发的时候,后者的军队中的大部分苏丹士兵就叛变了,战争计划也因此废弃。
再往北的地方,基钦纳率领着7500名英国士兵和12500名埃及士兵组成的联合军队向前稳步推进,由一支河上的炮艇队提供支持。战争的高潮出现在1898年9月2日恩图曼附近平原上,此处哈里发的军队发动了一系列的正面进攻。远程步枪、机枪和炮火击退了所有的攻击,夺去了11000名安萨尔的生命,并打伤了另外的16000人。这无异于一场大屠杀。比起欧洲和本土军队之间的任何其他遭遇,这更能说明工业化大国的技术和他们在非洲和亚洲对手之间的差距。这一差异是由当时仍是年轻中尉的温斯顿·丘吉尔总结的。除去参谋之外,他还担任战地记者的职责。第一次看到举着旗帜的安萨尔军队、穿着铠甲的骑兵和大量的矛兵和剑士,使他立即想到了所见过的12世纪十字军的图片。
在恩图曼战役后的那天,在喀土穆总督的宫殿遗址上象征性地升起了英国和埃及国旗。他们也为它的最后一个居住者戈登召开了追悼会。一个天主教牧师向上帝祈祷:“用怜悯和同情的眼神……向下看。这一英勇的灵魂对这片土地是如此地热爱。”这些话令基钦纳和其他官员感动得流泪。令丘吉尔厌恶的是,在战场上没有神之怜悯的象征,基钦纳任由受伤的安萨尔死去。在喀土穆,基钦纳带头抢劫。同时,许多哈里发的主要追随者立即遭到枪杀。其中的一些是在上尉、即后来的将军约翰·麦斯威尔(John Maxwell)爵士的命令下遭到射杀的。他在之后评论道,只有“死去的狂热分子才能激起他的同情”。1916年,作为英军在爱尔兰的总司令,他将同样的原则应用在复活节起义后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身上。
在恩图曼和喀土穆的暴行促使一群议员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反对向基钦纳支付三万英镑,以作为他在苏丹工作的奖赏。关于基钦纳掘出马赫迪的骨头一事,议员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考虑了几分钟是否要把头骨当作奖杯陈列之后,他就将骨头扔进了尼罗河。一位曾经做过官员的保守党议员对所谓不人道的指控嗤之以鼻,并提醒议院,“我们把文明带给了黑暗大陆”以及“妨碍一个国家实现其命运是致命的”。当一位自由主义者断言,“帝国主义不过是有组织的自私的时候”,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迈克尔·狄龙(Michael Dillon)反驳道,“杀人、抢劫、威士忌和《圣经》”都是这一文明的成分。就像其他该类型的辩论一样,这一辩论对指挥官来说是一种警示,在发动文明的战争的同时不抛弃文明行为规则。但是,投票结果有利于基钦纳,而他则得到了现金。
他把其中的一些金钱投给了他的心血结晶、英国文化使命的可见象征的喀土穆戈登纪念中学。这一机构的其他捐赠者当中包括制造机枪的厂家“维氏父子公司(Vickers Son)和马克沁(Maxim)”公司。与许多人一样,他们花费了大量精力以促成文明在苏丹的胜利。
占领喀土穆后不久,苏丹的政治前途就遭到了封堵;此后,此省就将通过一位英国总督由英国和埃及来联合管理了。这成了法绍达的遗留问题。马赫迪的囚犯已经向基钦纳透露了马尔尚在法绍达的存在。总司令已经得到了秘密命令,如果他在南苏丹遇到法国入侵者将如何行事。他应当驱逐法国人,但不直接使用武力。私下里,基钦纳认为马尔尚的恶作剧是一场“趣歌剧(opéra bouffe)”,不必当真。但当他遇见礼貌对待他的法国人的时候,他机智地将埃及国旗而不是英国国旗悬挂在法绍达上空。面对坚定和压倒性的力量,马尔尚退出了,并相信他维护了自己和国家的荣誉。
英国和法国之间随后爆发了一场国际性的争辩,双方都有大量好战的声音。由于在法绍达蒙受了失败和屈辱,法国政府指责英国在南苏丹违反其权利并欺负它的代表。英国拒绝了这些指控,并坚持认为法国对尼罗河上游的任何一部分都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大众既因恩图曼的胜利得意,又对近期在远东地区的让步感到不满,因而支持政府的坚定政策。英国必须在法绍达问题上形成一个立场,因为其竞争对手肯定会将任何妥协理解为对手犹豫的证据,并因此得到鼓励,去挑战英国在其他地方的权力。
英帝国会显得不可动摇,而法国则下台了。它别无选择,因为它的人民因德莱弗斯丑闻而分裂,而它的盟友俄罗斯则拒绝卷入在非洲中部的争论。此外,正如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卡塞所理解的那样,英国海军优势将使任何战争成为一场实力悬殊的比赛,法国的海外贸易将遭受类似于18世纪的英国所造成过的损害。它也明白,与英国作对,甚至将其作为德国的盟友的时候,法国在欧洲的力量都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
作为尼罗河斗争的胜利者,英国和其伙伴埃及不得不完成一项任务,即安抚和统治一个巨大且未开化地区的任务。此处居民此前对外界统治知之甚少。在恩图曼战役之后,哈里发率领着约一万名安萨尔逃到南苏丹。1899年11月,英军终于找到了他的踪迹,并在乌姆·杜威克拉(Umm Diwaykarat)战役中击败了他。安萨尔显然没有从恩图曼战役中吸取任何教训,他们再次投身步枪和机枪所营造的杀伤区,以数百人为单位地倒下了。就像在恩图曼的前例一样,将这一战争与集体自杀行为联系起来是不会太牵强的。他们宁死也不愿服从异教徒的统治。哈里发当然拥有纠正军事平衡的部分手段,因为他精心保存着1884-1885年战争中所俘获的现代武器。同样不平常的是英国指挥官无法理解他们在苏丹战役中目睹的意义。后来的陆军元帅黑格勋爵(Lord Haig)上尉发现了现代火力在恩图曼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但是作为1915和1918年间的西线总司令,他批准在英国军队发动攻击,并与哈里发的托钵僧面临同样的境遇。
恩图曼战役后近20年里,马赫迪和泛伊斯兰叛乱仍时有发生。最具威胁的是1916年由达尔富尔地区半自治苏丹阿里·第纳尔(Ali Dinar)领导的叛乱。他希望得到土德联军的援助,但却没有得到。在英国宣传中,他被塑造为一个疯子,几乎所有拒绝英国在非洲和亚洲统治的穆斯林都会得到这一评价。1898到1920年间,一直在索马里兰反对英国统治的穆罕默德·阿布杜勒·哈桑(Mhammed Abdille Hassan)得到了“疯狂的毛拉”的称号。在西北边境上,还有其他“疯狂”的托钵僧和毛拉。他们的暴行看似难以与阿里·第纳尔比肩。雷金纳德·温盖特爵士向美国新闻记者透露,这个人曾强迫母亲吃自己的孩子。我们无法得知,记者是否问过他,为什么英国人在过去的18年里容忍了这个达尔富尔怪物的存在这一问题。
英国人花了三十多年才征服了本能反对新式税收的南苏丹拜物教部落。他们也拒绝放弃偷盗牛马以及部落间争斗的习俗。需要33次惩罚性远征才能说服边远的努巴山区部落接受新秩序。没有记者随从分遣队,所以公众对这些战争中发生了什么一无所知。对于喀土穆和开罗当局来说,情况也是如此。“越不注意这些问题越好。”在读了一个有关1908年镇压苏丹小型起义后公开绞刑的报道后,克罗默勋爵评论道。另一种形式的威慑力于1928年施加。在喀土穆的一次访问中,丁卡(Dinka)和古尔(Guer)酋长参观了机枪和火炮展览。
不耐烦的官员往往采取更有力的压迫方法。1917到1918年,在努巴山区的行动中,村庄和庄稼遭到烧毁,部落民及家人则被赶入树林渴死。在温盖特的建议下,飞机从埃及到来,轰炸并扫射阿里第纳尔的军队。此后,他们经常与苏丹最南方的部落作战。效果是惊人的。1920年2月,燃烧弹落开始落在树林里,燃起了大火并迫使努尔战士离开阵地。此后,英国人对他们及其牲畜进行轰炸和扫射。伤亡人数通常很多(1928年1月,在一次对加扎勒贾布尔Bahr-al-Jabal的突围中,200人丧生)。但正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受害者一样,这些人没有那么容易屈服。
实施这些苛刻措施的官方理由是,他们给偏远和动荡的地区带来了稳定。然而,飞机轰炸令一些人感到深深的反感,他们认为,英国本声称,她希望给此地的人民第二次生命,但她实际上却使用了飞机去恐吓他们。被教育要相信自己国家的文化使命并为之献身的官员们,为“空中控制”这一委婉称呼而感到羞愧万分。1930年后,飞机轰炸暂停了,然而飞机仍旧在潜在不满地区的上空盘旋,提醒当地人不听话的下场是什么。正如喀土穆陷落之后的事件一样,这种短暂地利用空中力量作为惩罚手段的方法,显示出英帝国主义崇高的、人道主义的理想与代理人所采取方法之间的鸿沟。

免责声明
本站部分内容来自于网络或者相关专家观点,本站发表仅供历史爱好者学习参考,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本文地址:/sjls/lgsz/283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