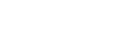约公元1000年
约莫是伊本·西拿人在布哈拉念哲学之时,有艘船在东南方大概六千英里的爪哇海上沉没了。一千年的历史距离,让我们无法确切得知发生了什么事。但某几种风险可以忽略不计。船航离岸边四十五英里开外,附近也没有任何礁岩。其实,这里的海床是一片平坦无物的泥土。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才是最有可能的飞来横祸。或许这是艘旧船,船身并没有弯曲,而是断裂。这些姓名不详的水手与商人距离他们在西爪哇岛的港口只差一百五十英里。他们没有留下任何回忆录,留下来的,只有他们的骨骸和财物。不过,近来的研究成果却能让我们像读回忆录般解读这艘遇难的船只,同时追溯这些货物的源头,其中有些货物的产地甚至远到伊本·法德兰与伊本·西拿身处的中东地区。01
这是艘什么类型的船?船是木造的,用的是东南亚的木材与设计。整艘船全长九十英尺(1英尺合0.3048米)、宽二十五英尺,吃水三百吨,采用的不是典型中国船只的平底,而是V型的龙骨。这艘船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色,在于造船的人没有使用铁制的材料。他们先是凿刻好龙骨,接着裁出弯曲的木板并排列整齐,用来构成船身,排好的木板则靠边上的暗榫接合在一起。造船师傅在木板的内侧留好对准位置的记号,然后打眼。横梁(桨手的坐板)放上来以后,再用棕榈纤维编的绳子跟做了记号的位置紧紧绑在一起。坐板之间垂直捆绑着,好让板材保持牢靠。这些船多半用三到四面帆,在船的其中一侧后四分之三的地方还有一具大型的舵。10 世纪时,这样的船只在东南亚的大岛港口与小岛之间定期航行,数量即便没有上千,也有上百。02 这些船使用当地原料,轻巧优雅的设计让它们能在大浪中曲屈,却不会粉碎。03
当时没有沉船打捞这回事,就连最值钱的货物,也在南中国海海底躺了上千年。船蛆吃了外露的木材,船货散了出来,最重的沉在一起,轻一点的东西则飘得愈来愈远。船的残骸虽然饱经腐蚀,却保护底下的黏土不受海流冲刷,最终在海床上形成了小丘。
是鸟找到了沉船。当地渔民看见了群集的水鸟。哪里有鸟,哪里就有鱼。任何从海床中搅动出来的东西周围都会有鱼聚集。印尼渔民知道,无论在开放海域的哪个地方捕到珊瑚礁鱼种,底下都可能有沉船;他们也都知道,沉船上的陶瓷器与人工制品要比鱼值钱得太多了。
1996年,雅加达古董店出现了一批古代陶瓷器,这让政府警觉到有人找到了沉船。船骸所在的深度(七十五英尺)与相对短的潜水季节拖慢了抢宝的步调,也让海军有时间逮捕潜水者。印尼政府沉船打捞委员会指派当地的打捞公司与一支德国挖掘队合作,进行全面的考古行动。考古队伍框定了遗址位置,打捞起超过两千七百件的重要历史文物。04
船底有上千磅(1磅合0.4536千克)的锡,全都是出产于马来半岛西北部的吉打(Kedah)、做上了记号的矮胖金字塔形小锡块。10 世纪时,锡就像金一样是开采出来的。人们磨碎、清洗含有锡的矿石——而且很可能都是以手工的方式进行——比较重的氧化锡则会沉到洗矿槽底。矿工也会到河里淘含有锡的卵石。这两种方式生产的氧化锡接下来都会被熔成锡锭。沉船上的锡锭是要运到爪哇的,因为当地完全不产金属。
在船难发生的年代,青铜是一种用途相当广泛的金属,而锡是青铜的原料,也因此非常重要。人们用青铜铸成雕像与宗教器物、臼和门链等简单的家用物品、珠宝,以及武器。印度、中东以及东南亚等地都有铸造含锡量高的青铜钱币。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人对吉打也不陌生。地理学者阿布·达拉夫(Abu Dalaf)便在公元940年写道:“全世界没有哪里的锡矿能够跟卡拉(Kalah,指吉打)的一较高下。”05
船上有许多部分含锡的商品。海床上有两批镜子。其中一批质量较差,是典型的印尼设计。另一批质量较好的镜子则产于中国。对于这两批镜子来说,锡都是重要的材料。中国制的镜子含有百分之二十五的锡,加入铜与铅中。06 这种混合方式创造出了一种质硬且脆的金属,兼有光彩动人的打磨镜面。看起来,马来地区的锡是以锡锭的形状被运到中国,熔制成特殊的合金,然后铸成像镜子这样的高价商品,其中有一些更是再出口到东南亚。10 世纪的东南亚有几个大型王国。中南半岛上有四个:新出现在上缅甸的蒲甘(Pagan)、柬埔寨的吴哥、越南中南部的占婆(Champa),以及稍后出现在越南北部的大越。07 这几个王国皆仰赖稻米种植,以首都邻近地区增加的人口为立国根本,它们也都是发展成熟、宫廷仪式繁复之地。08 岛屿上,则有掌握着贸易的室利佛逝(Srivijaya),这个难以捉摸的政权或许是以苏门答腊为其根据地。至于爪哇岛中部的国家马塔兰(Mataram),今天的学者对其国力与大小的看法分歧仍深;马塔兰显然是以无灌溉的稻米种植为经济基础,这个国家还打造了婆罗浮屠(Borobudur)—一座小山丘,上面铺满了雕有佛教主题的石板。09 婆罗浮屠上有块石板,上面刻画了一名衣着考究的宫廷女子,这名女子正用沉船上找到的那种镜子来化妆、绑头发。10 而她所穿戴的珠宝,也与沉船地点找到的三十多个金戒指、无数的金耳环、坠饰与串珠有着类似的风格。由此可知,锡与金对这段时间整个东南亚的宫廷文化展现都很关键。

中国制的镜子仅仅暗示了锡贸易的复杂程度,以及青铜器对思想与文化表现的重要性。负责打捞工作的潜水员也捞起了一尊小小的青铜佛陀立像。佛像的风格与当时印度东部的风格非常类似。11 由于孟加拉不产锡,商人很有可能把吉打的锡带到孟加拉,在那里熔制合金,并铸成这种雕像。船上还载了几个用来做小型佛龛的模子。这种迷你佛龛是以青铜或陶瓷为材料,在爪哇当地制成,供佛教徒所用;它们也跟那位拿着自己镜子的小姐一样,出现在婆罗浮屠山上的石板雕刻上。
沉船上找到的佛像,让一段悠久的传统跃然纸上。10 世纪时,佛教与印度教的法器与思想已经沿贸易路线来到东南亚,时间至少有五百年以上了。在玄奘印度行之前的一个世纪,一位名叫法显的中国朝圣僧也怀抱着对佛典的类似追寻,去了印度。他搭乘一艘印度船只,借道于经由整个东南亚的水路回到了中国。假如他曾探访过缅甸、印尼、泰国、越南、柬埔寨与老挝的话,他一定会碰上许多历史悠久的佛寺、佛塔与挂单处,就跟在丝路上以及印度当地一样。12 至少在10世纪以前,东南亚的各个大王国都有了显著的佛教或印度教特征。东南亚的国王们一如丝路沿线的王者,同样在佛教信仰中发现了共通的好处—超越族群忠诚的王权新愿景,以及一连串能促进贸易的场所。13
佛教也像在丝路与印度那样,与东南亚当地的传统融合在一起。比方说,虽然柬埔寨吴哥王国(公元802年至1432年)与印度的佛教建筑在风格上有许多类似之处,但它们却有不同的作用。这些建筑不是为了某种佛舍利,比方说佛牙、佛陀僧衣的碎片,或是佛陀的乞食钵而建。吴哥多数的大型建筑是盖来作为先王的陵墓用的,通常是由先王的继承人所兴建。碑文都在称颂先王,仅略为提及佛陀。这种祖先崇拜是东南亚的特色,并非佛教重镇印度的作风。14
东南亚地区和当时佛教的各个支派都有互动。 15打捞沉船的人找到了一大堆与金刚乘[Vajrayana,或称谭崔佛教(Tantric Buddhism)] 有关的法器,例如法铃以及独一无二的矛形权杖。这些教派在印度东部有长远的历史,但在10世纪的东南亚也同样兴盛,同时与其他发展更早的佛教教派为了得到赞助而竞争。佛教的金刚乘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传入了西藏。而9世纪爪哇中部婆罗浮屠的佛教遗迹里,赞助人委托雕塑在好几块石板上的,恰好就是这种权杖。16
船上的其他器物似乎和一些发源于印度的仪式有关:如青铜制狮头尖饰、青铜制莲花花苞,以及仪式用的长矛与杯盘。几样东西中最让人赞叹的,是一对镂空雕花的黄铜门链与门饰。木头的部分腐朽了,但黄铜配件的大小对一般房子来说却又太大。17 这扇门或许是为了爪哇岛上某个香火鼎盛的宗教圣地而造。许许多多的印度教与佛教教派都在竞争王室的赞助与信徒的数量。 这种盘根错节的宗教实践与政治对抗,似乎跟伊本·法德兰与伊本·西拿两人经历过的伊斯兰派系紧张相当类似。
最后一点:锡显然也熔在一开始放在船舱里的上千磅青铜合金锭里。这些青铜块全都是圆顶状,但大小或重量并不一致。青铜熔化之后,会倒进沙地上简单挖的坑里。考古证据暗示这些金属锭并非用新开采的矿石所制,而是用熔化的青铜器浇铸而成。放在货舱的这些青铜锭旁边还有一些青铜器的破片。这些破片或许只是还没有熔铸成块状,而且有可能正在被送往爪哇的路上,似乎是要用来再造为各式各样的家庭用品与神器。
整套复杂的锡贸易除了一开始的采矿与冶炼以外,还包括搜集破损的青铜器,把它们熔铸成锭,用船运到整个亚洲世界,然后重新铸成新的器具,而这或许是几个世纪以来一再重复的过程。每一磅所耗费的大量人力资源都让青铜变得非常贵重,贵重到回收再利用的做法成为经济上的必然措施。18 除了青铜以外,黄铜破片以及铜锌合金也大量出现在船舱里。而金属器的回收利用与重铸,也让我们很难分辨当时任何一件器物是从遥远的地方而来,还是在当地制造。
海床上还找到另一种金属锭—来自中国的银。有些银锭上的刻文写着“盐税上色银伍拾贰两专知官陈训”。银发现的情况与锡不同,锡锭集中在沉船地点中心,而银却在考古区中许多地方被发现,这表示银不是装在一块儿;或许是船上好几名商人各自带了几块。19 潜水员还找到四散各处的中国银币,以及数量不满一握的金币。商人进行交易时显然无须大量中国货币。沉船没有出现大量的外地货币,暗示了商人是以情势相对稳定的地方大型王国的通货来进行交易。
船上的铁也同样来自中国,包括铁锭、铁锅与铁制枪尖。当时只有中国具备高效的铸铁工序,能和东南亚产铁地区的当地制造者竞争。考古学家过去从大多数殖民时代前的东南亚沉船与陆地遗址中,都曾找到过中国铸铁锅。20 就以爪哇为例,当地在印坦沉船之后好几百年的时间都未曾生产铁。即便爪哇岛上有些许铁矿床,但当地却只进口其所需。21
潜水员取出超过两百四十五颗玻璃珠,珠子的大小、风格类似;最有趣的一点是这些珠子都是“有眼”的珠子。有一种制作玻璃珠的方法是把熔化的玻璃搓成小球。玻璃工会在玻璃还软的时候,把其他颜色的玻璃弄个好几小滴,并滴在表面上,弄出点点;然后再把另一种颜色的玻璃弄在每一个点点的中间。沉船地点的那堆玻璃珠里,主要的基底色有绿色、蓝色,少数则是棕色。点点则是白点中间加个蓝点。玻璃珠的化学成分与颜色都表明其产地在伊朗,而伊朗正是当时除了中国与印度以外唯一的玻璃制作地区。22 制作玻璃的技术已经在欧洲绝迹了好几个世纪,接下来还要两百多年才会再次出现。好几个位于泰国的考古遗址都曾挖掘出这种样式的“有眼”玻璃珠,制作年代也与沉船时代相近。23 玻璃珠子在靠近吉打的考古遗址中也很常见,而吉打正是马来半岛上与锡有关的地区。这些长途跋涉的“有眼”玻璃珠,则是用锡与锡贸易的利润所采买的其中一种商品。
玻璃珠的买卖就像锡贸易一样,不仅复杂,而且早在沉船的时代以前就有长久的历史了。从东南亚考古挖掘中找到的最早外来商品里就有各种珠子。其中有几个甚至能上溯至公元前的遗址里曾挖掘出的产自印度、风格别具的光玉髓珠。24 这类珠子出现在几乎所有大城市的挖掘现场,以及许许多多平淡无奇的遗迹里,时间都在沉船事件前的这一千年间。有充足的考古证据显示,直到10世纪为止,东南亚都是制作玻璃珠甚至是“有眼”玻璃珠的中心。但这些制造中心似乎只把进口的玻璃拿来做玻璃珠,本身却不熔制玻璃。沉船上也有证据能支持这种观点。潜水员在离玻璃珠不远的地方找到许多件玻璃器皿,只有极少数保持完整。考古队试图把这些器皿拼回去时,情况就很清楚了:船上运送的大多数玻璃器本来就是破片。这些或许就是东南亚制作玻璃珠的原物料。
沉船中的陶瓷器间接表明了日常用品在跨洋贸易中的重要性。考古队发现了相对少量的中国精制家用陶瓷器,如陶瓷罐、陶瓷锅与陶瓷碗。它们的数量完全被七千件粗制家用陶瓷器给压过了。多数的精制陶瓷器原先是成套成组的碗盘器皿,在今天被称为越瓷,产自现名浙江绍兴市的各个窑场。有一处时代稍早、同样做陶瓷买卖的沉船残骸中曾有六万件陶瓷器出土,其中主要都是来自同一个地区的普通陶瓷碗。25 至于沉船上其他会朽坏的东西呢?船上有三十二个铜制大锅。铜很容易受海水侵蚀,因此残余下来的只有铜锅的把手。船上还有一批坚硬含油的石栗,在海里待了一千年后居然还保持完整,而石栗也表明了大多数的船货其实都很稀松平常。人们至今还用类似的坚果来榨灯油。
其他考古证据暗示船货中可能有两种值钱的织品,很可惜并没有在沉船里找到。我们几乎可以确定船上一定有丝,这是爪哇与苏门答腊的风雅宫廷里非常热衷的东西。10 世纪时—也就是船难发生的时候—丝绸是从中国到西班牙宫廷生活中的衣着材质首选。丝和陶瓷器一样,都是中国出口商品的重中之重。虽说丝原产于中国,但到了船难发生时,也还有其他的产丝中心。立足未稳的欧洲产丝业在公元500年左右夭折,但在丝路的绿洲城镇以及中东城市里,养蚕知识与抽丝仍在继续。尽管面临这些竞争,中国还是主宰了大半的丝绸贸易,尤其是在东南亚。中国制造奢华的丝织品,还掌握了各地的审美观、气候以及用途。根据许多婆罗浮屠塔庙的石板,上面所刻的织品的垂挂皱褶暗示其为丝制品。在船难发生时的爪哇,上朝的贵族都穿丝绸衣服。等到有钱的平民百姓也开始买丝时,国王便觉得有必要颁布法律,限制只有贵族能穿戴丝绸与特定颜色的衣服。26 他们这么做,八成是为了在贵族与平民间维持一眼就看得出来的区别,同时防止阶层差异变得模糊。
棉花是印度的主要出口商品,我们也几乎能肯定船上一定载有棉花。有许多来自中东与中国、与船难同时期的文书曾提到印度的棉花。人们近来也发现了更直接明确,也更令人雀跃不已的考古证据。好几个福斯塔特(位于开罗南方)旧城垃圾场的考古挖掘地,都挖掘出了上百件有压印图案的棉织品碎片,时间最远可追溯至11世纪,也有不少是来自接下来的两个世纪。开罗地区干燥的气候让这些碎布保存了将近千年之久。对捻线方式、收边风格与木版印刷图案的分析,确定了这些碎布来自印度西海岸的古吉拉特(Gujarat)。这些小碎棉布来自简便的功能性衣物,与印尼当地运用丝绸的方式非常不同。古吉拉特就像中国地区生产陶瓷的浙江省,有许多专业化的产棉、棉染、棉织中心密布于乡间。27
船难发生时,古吉拉特的各个口岸出口棉织品的传统已经相当悠久了。棉花种植与织布的情况一如丝绸,早已沿贸易路线传遍了整个亚洲世界。比方说,10世纪的爪哇就有种植棉花、织棉布。古吉拉特当地对此的反应也跟中国相去不远,会针对远方市场的需求做出细微调整。研究人员最近在东南亚岛屿上找到了大致完好的衣物,其编织和收边方式与在埃及找到的碎布完全吻合。不同之处在于颜色与雕版印刷的花纹。红色的花纹显然在印尼销量很好,而蓝色在东南亚是种不祥的颜色,蓝色花纹也就从未出现过。绿色花纹在埃及卖得不错。至于动物花纹的衣服,会运到东南亚,但不会送到信奉伊斯兰信仰的埃及。这些考古发现暗示商人不单是把古吉拉特的棉布带到遥远的土地,巴望能卖出去。情况正好相反,关于“哪些商品卖得好,哪些卖得不好”,会有详细的情报从商人那儿回流给生产商。甚至还有考古证据证明有人把印尼的花样带回古吉拉特模仿,以满足市场口味。28
在种种通常会朽坏的文物里,最让人垂思不已的或许是平常难得能发现的四十四具人类骨骸。小船沉没时,船员与乘客通常都会试着从船上逃出去;至于逃生不及的那些人,海流一般也会把他们的遗体带离沉船的地点。船要沉的时候,这些倒霉的人为什么不下船?或许他们正在底下的甲板睡觉,但他们同样很可能是被关在下面甲板的奴隶。奴隶制—有着诸多形式与诸多目的—相当普遍。东南亚就像前文提到的草原地区一样地广人稀。对于每一个想增加人口的部落或王国来说,奴役被征服者或战败者,是种行之有年的做法。亚洲的奴隶制度里囊括了奴隶主与男奴或女奴间极为多样的法律关系与实质关系—无论是在家里、商业活动中、军队中还是宫廷中皆然。奴隶也像朝圣者、商人与使节一样,在整个亚洲世界里大批大批地移动。
沉船上只留下了一些与船上其他人有关的线索。潜水员找到许多久经使用的锐利石器,这些石器很可能是水手的物品,他们打磨自己的剑和小刀来打发时间。东南亚当地就像印度东西两侧的海岸地区,那里的水手与海盗之间没有什么差别。水手跟海盗都有武器,而他们之间的不同,则要看谁才是货物或船的所有人。海盗是个挥之不去的问题,连一些与沉船同时代的东南亚碑文上都曾提到过。29 至于其他有关船员的线索,就只有几口用过的锅、一个鱼钩和三套杵臼。
有些少数形状特殊的青铜尖饰,是某个特定佛教教派的僧人手杖的特色。僧侣一如在玄奘的时代,从一个寺院到另一个寺院去追寻学问。晚近的研究重建了当时北印度的菩提伽耶、缅甸与斯里兰卡间的交流。30 散落在整处遗址的个别几只金戒指,再加上偶然找到的、为贵金属称重用的小天秤,都暗示船上有富有的商人。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说明这些商人是何许人也,但他们或许都出身于东南亚。考虑到爪哇当时前后的碑文曾提到来自柬埔寨、缅甸以及印度好几个地区的商人,或许也有些商人是来自更遥远的地方。31 僧侣与商人有可能都识字,但直接的证据就只有潜水员找到的一些戒指,上面有蜡封,蜡封上还有字迹。
这艘船是从哪里载来种类与产地如此多元的货物?所有的货物显然都是在苏门答腊的某个转口港上船的,或许是巨港(Palembang)。货物从四面八方来到单一口岸——商人则在港口这里存放、集中这些商品——成为要运往许多不同口岸的船货。这是当时整个亚洲海上贸易的特性。在东南亚的西部,人们偏好的转口港位置会随航海技术的发展而改变。在玄奘的时代,也就是公元400年至600年前后,当时的水手显然并不具备在苏门答腊沿岸沙洲间航行的工具或技术,也无法克服马六甲海峡的海盗问题。他们把要送往印度洋的货物,在马来半岛上一个叫作克拉地峡(Isthmus of Kra)的狭窄地方卸货;会有人用河运把商品载到半岛的西侧。
到了10世纪时,航海技术已经有了进步,航线与港口也随之变化。登上沉船后,潜水员找到了一只罗盘碗。这项技术上的突破虽然来自中国,但也已经传遍了整个东南亚,更沿着航道传到了当时的印度。指南针是用一小块天然的磁石,也就是磁化后的铁所制,磁石安在一个小木盘上。人们后来让这种轻便的工具浮在碗里,碗壁内侧则刻上记号。罗盘极为常见。这艘沉船不过就是艘不甚特别的货船,船上就有这么一个罗盘。32 在沉船事件前的几百年间,船帆与船舵可能也有相当的进步。
在东南亚的岛屿上,有几个王国为了发展与控制重要港口以及随之而来的贸易税而竞争。船难发生时,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是最强大的海权国家,掌握了最重要的转口港。但在1025年,南印度的一个帝国袭击了室利佛逝,终结了该国对贸易的支配。接下来,有好几个港口为了转口贸易而互相对抗了数百年。
最后是马六甲在14世纪与15世纪时脱颖而出。33
爪哇拥有足以分配进口货物的完善建设,同时也是印坦这艘沉船理所当然的目的地。虽然没有大都市,但爪哇城镇与村落在指定的日子都有常态的市集。当时的碑文列出了商人的身份、买卖的商品、要缴什么种类的税,暗示了这一批批的专业贸易商会在超过一个以上的市集,甚至是到好几个城镇中进行交易。(农业税须以现金缴纳,这意味着地方上有足够的现金用来购买进口商品。)地方上的商人在这些常设市集里活动,也正是他们把来自中国的煮饭锅以及日常用的陶瓷器(中国和爪哇做的都有)带进岛内深处。就像亚洲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有冒险精神的地方商人也会生产外国进口货的便宜仿冒品。爪哇当地的陶瓷器对中国的样式亦步亦趋。34 至于货款要怎么打平?假设这艘船没有沉,那会载什么回转口港,或是载去其他港口,好用来为陶瓷器、丝绸、锡、棉花和其他商品付账?中国当时的官府文书上记载了人们对各种东南亚的芳香树脂、香料与木材永不餍足的需求。官员非常关注为了买这些林产而流失的中国银两,于是建议促进陶瓷业发展,用来卖给东南亚。沉船上这些式样朴素的大量陶瓷器,就暗示了这样的政策不仅曾付诸实行,而且卓有成效。35
芳香剂在整个亚洲世界都是重要的商品。中国与印度在宗教上以及家屋、宫廷、庙宇和墓地里的日常仪式上都需要用香,而有香味的树脂与木材正是制香的基本材料。来自东南亚的芳香剂既是当时入药与医疗上的重要材料,也是身上用的香水与精油的成分。从东南亚一路到中东,这些芳香剂都是所费不赀的交易商品,欧洲教堂里的香炉也需要盛装它们。但在沉船遗址,只有二十四小块的安息香能间接证实这种重要贸易的存在;安息香是东南亚的一种树脂,广泛应用在佛寺与家户的仪式里。36 船上原本应该还有更多,但洋流可能已经把这些重量轻的东西带走了。
沉船里移动距离最远的人工制品是一小堆陶瓷器,而且全都碎了。从陶瓷器上的土耳其蓝釉面与釉裂来看,这肯定是伊斯兰世界的产物,而且一定是来自中东地区,很可能就是伊本·法德兰所在的巴格达。不过,沿海路旅行到东南亚的可不只有伊斯兰国度的制品。早在船难发生前两个世纪,阿拉伯水手便已经造访了东南亚与中国,至今仍有若干传世文献。这两百年间,穆斯林商人一路上建立了好几个小型的居住社群,盖起了清真寺。穆斯林教士与法学家也逐渐迁居到这些港口来服务会众。伊斯兰信仰沿着海路吸引新的信徒:从印度西海岸到东南亚港口,然后则是中国南方口岸。与此同时,伊斯兰信仰也在中亚商旅城市以及中国北方得到新信徒。伊斯兰信仰沿贸易路线散播的模式,似乎与佛教的传播非常相似。
对于大亚洲世界的南方水路沿线贸易来说,这艘10世纪沉船里的金属锭和人工制品意味着什么?中东、印度与中国地区大型王国的发展,加上品位相对讲究的城市居民,共同创造了对黄金、象牙、丝绸与珍珠等奢侈品的需求,而这些商品正是“富饶东方”的代表性商品。37 至于贸易路线上与这些奢侈品同样重要的,则是有关宗教信仰的物品—经书、神像、绘画、法铃,诸如此类。这些商品都是由专业化的中心所生产。带着这些物品千里跋涉的通常都是僧人,借以撑起跨洲的知识与心灵纽带。但是,若与奢侈品或宗教器物的买卖相比,平凡无奇的区域性商品或许更有经济上的价值。船只则载运鱼酱、稻米、日用陶瓷器、铁罐与锡。
奢侈品、宗教器物与日常用品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远超过城市中心与宫廷。人们的需求深入印度与东南亚的内陆森林、斯里兰卡的采珠业,以及位于古吉拉特乡间的成衣制造业。商业活动也不会只顺着宗教的边界发展。信奉佛教与印度教的东南亚所产的香,可是轻而易举地传播到信奉伊斯兰信仰的中东与尊崇儒家的中国。贸易商品也是宗教敬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船上那些所费不赀的门让人感受到当时东南亚岛上佛教寺院群体的繁荣、实力与活力。佛教金刚乘的法器则暗示了一个新教派的发展。
伊斯兰信仰也是新兴宗教,而且还沿着同样的路线在成长。总之,贸易是亚洲世界日常文化的根本。汉人的仪式需要东南亚的香,就跟爪哇宫廷也要用上进口的黄金一样。

免责声明
本站部分内容来自于网络或者相关专家观点,本站发表仅供历史爱好者学习参考,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本文地址:/sjls/lgsz/2701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