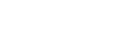公元1325年至1356年
公元1332年时,德里苏丹的王宫里有好几座庭院,还有个叫作哈扎尔·乌斯坦(Hazar Ustan)的大厅—意思是“千柱厅”。当时一位观察家写道:“用来支撑木造屋顶的柱子都是经过精雕细琢的上漆木头。苏丹就坐在铺着白地毯的讲台顶一把垫高的椅子上,背靠着一块大软垫,在他的左右手边还有其他两块靠垫。”01 苏丹的左右各有一百名侍卫。在苏丹跟前的是他手下最高级的官员,身后则是上百名贵族—全都穿着丝袍。城里的法官和穆斯林教师在四周各站了一排。大厅更外侧则是苏丹的远亲、低阶贵族,以及军事将领。
这样的阵仗有项特别的任务,是要把外国人引见给苏丹穆罕默德·图格鲁克(Muhammad Tughluq)。就在这一天,来自摩洛哥、初来乍到的伊本·巴图塔和同伴带着他们要给苏丹的礼物走上殿来。伊本·巴图塔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见识这种仪式好几次,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叙述道:
对伊本·巴图塔及其同伴来说,这天真是黄道吉日。苏丹待他们如上宾,还在治下的政府里给他们安排了适合的职位。而对伊本·巴图塔个人而言,面见苏丹则是一场高风险的赌局。他呈给苏丹的贵重礼物,是用从某个放款人那儿借来的钱买的,要想还得起钱,除了觅得他想要的官职以外就别无他法。对做买卖的人来说,谋得一官半职以前就先花钱买送给苏丹的大礼,这也是一笔类似风险资本的钱。03 在伊本·巴图塔以前,已经有数以千计的人冒过这种险了。
未及而立之年,伊本·巴图塔就带着一行将近四十人的随员来到了德里,里面有男奴、女奴、侍者与几个旅伴。他有上千匹马,好几箱上好的衣物,还有一群驮兽,包括骆驼。自从公元1325年6月离开摩洛哥以来,七年间他已经走过了漫长的路途,一心想继续前往麦加的朝圣之行,热切而坚定。
在一片凶险中,伊本·巴图塔从摩洛哥出发,对这回的旅行忧心忡忡。来自摩洛哥中部与突尼西亚的成群游牧民不时攻击商队,甚至还袭击城池。内心七上八下的他加入了一小群人,迅速前往安全的避风港—突尼斯。但当一行人抵达该地时,也没有人来迎接他。
他在突尼斯参加了由一位叫阿布·雅库布·苏萨(Abu Yaqub al-Susa)的人所组织的庞大朝圣队伍。沿岸地区仍然和2世纪以前亚伯拉罕·本·易尤在世时一样,饱受基督徒军队的劫掠。伊本·巴图塔引了一段当时诗人的话:“多少人丢了货物,失魂落魄,徘徊在陆地上!又有多少人在大海上度过他们的夜晚,哀叹沦落为奴、万劫不复!”06 一次次的袭击毁了突尼西亚的经济,盗贼蜂起。幸好队伍里有一支由百名弓箭手组成的部队,更有超过一百名的骑士陪他们走了一段路。
打从一开始,伊本·巴图塔似乎就有一种自抬身价的天分。人在队伍里的他,设法从一大群摩洛哥朝圣者中得到了“卡迪”(qazi)的职位,也就是伊斯兰律法法官与顾问的位子。07 伊本·巴图塔出身于法官世家。他受过的教育以及与生俱来的悟性,都有助于他在这样的机会里拔得头筹。虽然他不富有,但显然也不穷酸。朝圣队伍中有名来自突尼斯的治安官,伊本·巴图塔和治安官的女儿缔了婚约。队伍一面沿北非海岸前进,她也来到的黎波里与伊本·巴图塔相聚。但就在今天的利比亚东部,他“和我的岳父牵扯进一场纠纷,这让我非得和他的女儿分开不可”。伊本·巴图塔旋即再婚,这一回则是跟某位来自非斯(Fez)的学者的千金,而这学者人可能也在队伍里。一等到新娘在埃及海岸和伊本·巴图塔结为连理,他便“办了场婚宴,耽搁了整队人一整天的时间,款待了所有人”。08 但无论是这位妻子还是她所生的孩子,却再也没有出现在伊本·巴图塔四册自传余下的篇章里。或许,她只是又一次年轻时犯下的错,和她的父亲一块儿被送回非斯了。
亚伯拉罕·本·易尤晚年定居在开罗;过了几乎两百年后,开罗仍然是个大都市。
伊本·巴图塔骑着马,踏遍了尼罗河三角洲上的城镇,接着乘船逆尼罗河而上,打算跨过红海,完成往麦加的“朝觐”(hajj)。这趟悠闲的旅程在阿伊扎布—也就是亚伯拉罕·本·易尤跟他的代销人在两百年前为了三百迪拉姆起争执的同一个风沙漫天的港口—画下句点。时机实在不巧,统治阿伊扎布地区的家族正和开罗苏丹的军队打仗,不时击沉红海上的船只。伊本·巴图塔无法继续前行,只好乘船回转开罗。
伊本·巴图塔已经知道自己热爱旅行,其程度至少也跟研习宗教不相上下。他在行脚开罗期间发展出一套顺应这两种热情的做法。每到一座城市、一处城镇,他就去找有名的教士,和他们相处个几小时。他不像平常那些为追寻学问而旅行的人那样一待就是几个月,而是只听讲道,或是与他们交谈。他在尼罗河畔俄克喜林库斯[Oxyrhynchus,今巴纳萨(El Bahnasa)]的这次遭遇就颇具代表性:“我在那里见到的人当中,学养深厚的卡迪谢拉夫丁(Sharaf al-Din)是个内心高贵、值得深交的人,我还见到了虔诚的长老阿布·贝克尔·阿日马尼(Abu Bakr al-Ajmani),和他住在一块儿,做他的客人。”10 伊本·巴图塔在尼罗河岸的另一处城镇里,得到某位知名教士的一套推荐信,对此他格外珍惜。旅途中,他敞开心胸,学到的远远不只是信仰教条。他也尽可能与当地的杰出人士会面,至于见不到的人,就搜集他们的事迹,后来他在写故事与寓言时这些也全都派上了用场。伊本·巴图塔细细观察当地的圣坛、建筑、物产与风俗。他写道,尼罗河沿岸城镇中的布什(Bush)是“埃及亚麻生产的中心,亚麻就从这里出口到埃及与非洲(Africa)各地”。11 俄克喜林库斯是羊毛产业的中心,而迈莱维(Mallawi)镇上则有十一座营运中的轧糖厂。“他们从来不会阻止穷人踏进任何一间糖埠,于是穷人就会带着一块温热的面包来,把面包丢进煮糖的大锅里,再把吸满糖汁的面包从锅里挑出来,带着面包离开,这是当地人的习惯。”12

当时的每一座伊斯兰城市里,都能找到靠捐献所支持的招待所与学校[即伊斯兰学校(madrassas)];自从在亚历山大脱队之后,伊本·巴图塔就踏进了伊斯兰学校组成的网络里。对穆斯林精英而言,促进贸易、旅游与朝圣的行为是种虔诚、体面,有时甚至有利可图的做法。伊本·巴图塔还在尼罗河游历时,便称赞过沙希卜·塔吉丁·伊本·汉纳(Sahib Taj al-Din ibn Hanna)设在开罗南方、为所有受过教育的旅人提供食物的招待所。到了叙利亚的阿勒颇(Halab),伊本·巴图塔形容那里的清真寺在“这类建筑里是数一数二的富丽堂皇,讲坛还镶嵌着象牙与黑檀”,比邻的学校“在规划与建筑之美上”也能与之相辉映。13
这种由社会上层赞助的旅行与学习机构体系,听起来和玄奘造访过的佛教寺院有种奇妙的相似之处,而且说不定就是模仿佛寺而来。这一套支持着求道者旅行的体系就是起源于中亚,当地的佛教寺院资助旅人追求类似的目标已有千年之久。14 [伊斯兰信仰就像佛教一样,要求个人为了性灵的发展与学习踏上旅途。] 15每一位穆斯林都应该前往麦加朝圣一次,但严肃的学习可不仅止于此,更要前往不同的都市与学校,求教于各式各样的学者和教士。就在顺尼罗河而下的回转之行后,伊本·巴图塔仅仅在开罗停留了一晚,旋即动身踏上往北的陆路,沿今日的埃及、以色列与黎巴嫩海岸地区前往麦加。在前往大马士革途中,伊本·巴图塔还造访了阿科(Akko)、苏尔(Sour)、赛达(Saida)、特拉布洛西(Trablousi),以及位于内陆的圣城耶路撒冷。土耳其军队已经在公元1325年以前克复了这片海岸上所有的基督教军团国家,但基督徒与穆斯林军队间的战争仍然让许多地方满目疮痍。伊本·巴图塔写下了自己经过的城镇有哪些物产与特色:
伊本·巴图塔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描述大马士革清真寺的建筑奇观,一共写了八页,但他却用了更多的篇幅来谈自己拓展中的人际网络—清真寺的伊玛目、教师与知名人士:
在大马士革,伊本·巴图塔也参加了《圣训》(Sahih,记载先知言谈的经书,大约写于公元850年)的讲座,他自豪地写道,自己获得正式认证,可以讲授这部经。
如果回忆录里记载的时间正确无误,那伊本·巴图塔可真是个大忙人。他人只在大马士革待了二十二天。除了听讲以外,他甚至还梅开三度。这一回的婚姻带来了一个儿子,他的回忆录后来还提到过这孩子一次。伊本·巴图塔把自己身怀六甲的妻子留在大马士革,加入了一支庞大的朝圣队伍,前往圣城麦地那与麦加。
从穆罕默德的时代开始,前往麦加朝圣—也就是所谓的“朝觐”—就已经是每一位穆斯林所应尽的义务。到了14世纪,“朝觐”已经成了极有组织的旅游行程。由大马士革出发的行程一开始就是给养充足的休息站,以及与穆罕默德有所关联的遗迹,但中间也包括好几天的沙漠行,以及热浪与沙尘暴带来的危险。这支朝圣队伍在麦地那城停留了四天,穆罕默德一度在此讲道、生活。白天的时间就花在造访圣地之上。
到了夜晚时光,则是在城里的清真寺挨着烛火,聆听背诵《古兰经》的声音度过的。顺带一提,伊本·巴图塔的回忆录还告诉我们,麦地那大清真寺的天花板和镶金边饰都是用柚木所造,这些木头无疑是来自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19 朝圣队伍夜里下榻在水源充沛的村落,走了七天后终于抵达了麦加。“朝觐”之行的每一天,在麦加内外都有特别的活动。伊本·巴图塔和旅伴们首先去了麦加最神圣之地,克尔白。
算上四处晃荡和所绕的路,伊本·巴图塔花了十六个月才抵达麦加。
“朝觐”时,伊本·巴图塔与来自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人相遇。他遇到了一位叫曼沙德·本·沙伊克(Mansard bin Shaik of Medina)的麦地那人,之后他还会遇见这人两次,一次在叙利亚,一次则在布哈拉。还有一位同行朝圣的人,名为阿里·本·哈夏·乌玛威(Ali bin Hujr al-Umawi),来自西班牙的格拉纳达;后来在德里时,伊本·巴图塔也资助过他。21
多数的朝圣者在麦加经历一周的圣事后,就重拾了自己的日常生活。但伊本·巴图塔却留下来进修、建立人脉。留在麦加的这些年,伊本·巴图塔认识了在德里苏丹手下担任资深大使的人,他时常带着印度宫廷的捐赠,往来于印度与麦加之间。他还遇见同为法官的人,这人也来自其故乡—摩洛哥的陶亚(Tauja),是他父亲的友人。成千上万的人长途跋涉,追求教师、法官、教士、官员与士兵等工作,而伊本·巴图塔遇到的这些人,不过就是此情此景的缩影。
对受过教育的人来说,12世纪时头一遭出现了一个几乎无国界的世界。在这一大片从西班牙延伸到中国口岸城市的地区里,多的是四海为家的人。他们在法律与宗教教学上的能力在整个伊斯兰世界都派得上用场,整个伊斯兰世界也都需要他们的专长。许多城市吸引这些满腹经纶的旅人,他们也在自己的新家留下了印迹。伊本·巴图塔注意到,麦地那“那个掌管司法行政的人”来自突尼斯,而伊本·巴图塔的家人和那里的关系保持得不错。麦地那的学者则包括来自非斯、开罗与格拉纳达的人。大马士革的知名学者中,一位来自西班牙的塞维利亚(Seville),另一位则出身于摩洛哥的马拉喀什(Marrakech)。伊拉克南部马什德(Mashed)城里的政教领袖甚至有个在西班牙与直布罗陀工作、生活的兄弟。到了波斯的设拉子(Shiraz),伊本·巴图塔下榻在长老阿布·伊斯科(Abu Iasq)的招待所,而这位长老所收到的钱,则来自从中东经印度海岸直至中国这一路上的各个赞助人。22 整体而言,到外地找工作的人数相当庞大,很可能有数十万人。当时有超过数十座信奉伊斯兰教的大城市,数百座小城市,其中每一座都可能有工作机会。
在麦加过了一年后,伊本·巴图塔在“行遍天下”的渴望驱使下,再度加入了大商队之行。23 后来他花在慈善招待所的时间愈来愈少,陪伴王侯的时间则是愈来愈多,同时他也学到了宫廷礼仪与风俗。他离开巴格达,加入了苏丹不赛因(Abu Sa’id)的随员,为的则是“观察伊拉克王在其旅途与营寨中所能见识到的礼仪”。24 这位苏丹是帝国开基祖成吉思汗的五世孙,统治着当时大部分的中东地区。伊本·巴图塔仔细观察这位蒙古大汗日常生活中的仪礼,包括行伍、乐师、旗帜,以及贵族所参加的仪式,他还写到了这些贵族“漂亮的衣袍”。
他跟在国王身边将近两周时间,接着和国王底下的一位贵族旅行了十天,然后再回到国王的营帐里,“埃米尔在那里跟国王提起我,引介我到国王的面前。”等到“国王问起我的国家时”,伊本·巴图塔早就准备好一大堆的故事了。从这场会面中,他带走了“一件袍子、一匹马”,以及下一段旅程整段所需的“给养与马崽”。25 苏丹甚至还给巴格达总督,以及伊本·巴图塔旅程上另外两座城池的长官写了介绍信。
伊本·巴图塔对营帐里的仪式,以及苏丹不赛因的随员有相当深刻的印象。
接下来的六年,伊本·巴图塔在波斯、君士坦丁堡、克里米亚、高加索,以及今天的乌兹别克与阿富汗等地,精进自己在宫廷里的进退应对。他学会了人在马上、马下时要如何行礼。若从“一件埃及亚麻短袍、一件耶路撒冷制的皮披风”与“坎克(kamkha)是巴格达、大不里士(Tabriz)、内沙布尔与中国等地所生产的丝绸织品”等叙述看来,他显然很清楚当时上好布料的名字与产地。27 可汗送的华衮则让他上得了庙堂。他发现,无论他去到的是穆斯林、基督徒还是泛灵论者的宫廷,大半个亚洲的宫廷礼物都相去不远—包括丝袍、镶了宝石的兵器、金子、马匹以及奴隶。伊本·巴图塔只用了一两年的时间,就成了鉴赏马、鉴赏女奴的行家。他收送好几个女奴当作礼物,从大马士革到德里这迂回曲折的一路上也买了不少女奴。为了私人逸乐而购买妾室,是亚洲世界奴隶制度的另一面。伊本·巴图塔的回忆录里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女奴的名字,而女奴对他的随员来说似乎也不太重要。相较之下,他形容自己的旅伴时,还带着更多的热情与更多的细节。
无论是在大马士革,在整个土耳其与波斯,还是在印度的时候,伊本·巴图塔曾有几回待在不同的苏非教团(Sufi order)招待所。这些苏非行者是何许人也?苏非行者与穆斯林不同,他们(至今仍然)相信有直接、狂喜地体验神的可能性,而他们特别的仪轨—跳舞、唱诵、诗歌、命理学与玄秘的言谈—都是要让人处在这些体验有机会发生的状态。与真神的这种直接体验比每日的祷告或伊斯兰教法重要得多,但苏非行者多半仍恪守传统,当作在伊斯兰世界生活的实际要求。
一开始,苏非行者的中心是由数个独身的师父所组成,他们选择住在既有的招待所或商队的休息站,教导那些为追求知识而来来去去的人。在这些师父里,有少数人会发展出自己的修行法,师父过世后则由徒弟保存与发展。人们接着在各个徒弟定居的城市里找地方传授这些修行法,其中也包括让门徒们居住的房舍。他们迅速发展出神职体系来支持这些会所,处理捐献事宜、执事人员、规章等,并跟特定的教学中心联系在一起—这一切都不难想见。许多圣职变成代代相传的位子,捐献的来源也变成政府的赞助。28 早在伊本·巴图塔的时代以前,几个伊斯兰逊尼支派就接纳了苏非教义,用来补足他们自己这种更合法的教派,而不是将之视为威胁。到了14世纪时,某些苏非教团已有超过五百年的历史,但新的教派仍不时围绕着某个特别有影响力的师父而出现。
某些苏非教团只有地区性的发展,例如在北非或波斯,但有许多教团则散布到中东与中亚城镇,甚至还深入印度。等到蒙古人在公元1258年攻陷巴格达之后,苏非教团就真的大红大紫了。哈里发国这种伊斯兰信仰的中心机构从此销声匿迹。等到七十五年后,亦即伊本·巴图塔旅行时,一系列的苏非招待所与学校就是残存下来规模最大的伊斯兰信仰机构。
伊本·巴图塔很快注意到,有许多国王的仪式就跟宫廷中的礼物一样,是整个亚洲世界所共享的,甚至还超乎其上。他写道,有好几个宫廷都有赠予嚼食荖叶、槟榔的习俗。槟榔跟荖叶虽然原生于印度,但这种风俗倒是传遍了整个中东与东非海岸的宫廷。从国王手上接下槟榔,称得上是一个人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之一。29 伊本·巴图塔后来还会在东南亚与中国南部各地目睹这种国王授予槟榔的仪式。各国国王同样被一大堆共通的王室象征所包围,如阳伞、旌旗与大鼓。
这些象征与仪式跨越了语言、地区与宗教。
不久后,伊本·巴图塔就能对这一个国王谈另一个国王的事,这可是国王们求之若渴的情报。每一位国王都被敌人、派系、七嘴八舌的贵族,以及必不可少、却又颟顸驽钝的官僚制度给团团包围。他们也因此特别想去了解有效的策略、各种王权象征,以及其他宫廷里的仪式。从某种角度来看,伊本·巴图塔与国王的对话算得上是当时的经营管理讨论课,而伊本·巴图塔则是一位相当成功的管理顾问。也门王向伊本·巴图塔问起摩洛哥苏丹,“还有跟埃及王、伊拉克王以及洛尔人(Lurs) 的王有关的事,他也问了许多和这些国王有关的问题,我也一一回答了。他的维齐尔(vizier,高级行政官员,也作vazier)随侍一旁,国王命令他恭敬地接待我,还要帮我安排住处。”30
伊本·巴图塔还曾经游历过东非海岸,发现当地的宗教、贸易、风俗与亚洲世界是连在一起的。此地的几座大城是摩加迪沙(Mogadishu)、基尔瓦(Kilwa)、蒙巴萨(Mombasa)与桑给巴尔(Zanzibar),城里人都是穆斯林。当地的经济是以奴隶、金子、马匹出口(主要是对印度)以及进口印度棉花为基础。亚洲世界各地都在进口非洲象牙。伊本·巴图塔虽然觉得当地人新鲜,但风俗却很类似。摩加迪沙苏丹将槟榔与荣袍送给了伊本·巴图塔,而他是这么描写这件衣服的:

行至中亚深处,伊本·巴图塔拜访了一位苏丹,还收到了类似的礼物,用来答谢他所讲的诸王事迹。
伊本·巴图塔就是从这些国王的手上慢慢得到这些马匹、袍服、金子和毛皮。他收下了奴隶,接纳旅伴进入自己的队伍,随员数量也随之增长。
这就是伊本·巴图塔带来德里的那支由近四十个人、超过一千匹马,以及好几箱上好衣袍组成的队伍的由来。他成了“有头有脸”的人,有故事可说,有仪礼能讲述,对国王的任命也抱着合理的期待。在那个时候,伊本·巴图塔因为自己送苏丹的礼物而欠下了五万五千迪拉姆银币的债,但赌这一把看来是值得了。伊本·巴图塔在印度得到的,远比他人的庇护更有分量—就像许许多多的军人、教士与法官那样,他找到了工作。德里苏丹雇用他来担任城里大法官的一员,他就在这个酬劳丰厚的位子上坐了九年,历经饥荒、派系斗争与宫廷阴谋。33 虽然伊本·巴图塔不懂当地语言,但因为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伊斯兰教法大体上都是一样的,所以他才能够担任这个职位。34 而管理某座重要陵墓底下的慈善基金,也包括在他对国王应当负起的责任范围内。35 公元1341年,伊本·巴图塔离开德里,去完成最后一次外交任务,要把袍服、金子、奴隶与其他礼物从德里苏丹这里运往中国皇帝那里。一行人朝西南方横跨整个印度,抵达古吉拉特的主要港口肯帕德(Cambay)。伊本·巴图塔最后报告说礼物在船难中沉没了。当代学者质疑这趟任务的真实性,因为在中国或印度的记录中都没有相应的证据。无论如何,伊本·巴图塔是回不去德里了,于是他沿着西印度海岸前往马拉巴尔。在肯帕德、胡纳尔(Honar,靠近孟买)、卡利卡特与科钦,他找到了几个苏非教团的分支。当地的苏非门徒与平信徒将这几座城当作对中东的贸易网络。伊本·巴图塔在门格洛尔所见的香料贸易,就跟2世纪以前亚伯拉罕·本·易尤的时代的一样活跃。“多数来自法尔丝(Fars,即波斯)与亚曼(al-Yaman,即也门)的商人就是在这座城镇卸货,这里的胡椒和姜实在多不胜数。”36 伊本·巴图塔的回忆录不像亚伯拉罕的信,里面还包括对胡椒种植过程精准的描述,意趣横生。
伊本·巴图塔继续着他前往马尔代夫群岛与斯里兰卡的旅程。他宣称自己从斯里兰卡往东出发,途经东南亚,抵达中国。当代学者也怀疑这趟行程—不仅地理描述混乱,而且整段叙述有一大半都是用几桩可疑的个人遭遇故事编造而成。为了增添自己的威望,伊本·巴图塔有可能用自己听来的消息捏造了这趟旅途。
但马尔代夫的确才刚改宗伊斯兰信仰,伊本·巴图塔也曾造访当地,这倒毋庸置疑。他担任穆斯林法官,严正制裁那些不参加晚祷的人。伊本·巴图塔还延续了自己结露水姻缘的习惯,与当地人结婚;不到几个月,他就跟四位不同的名流仕女结为连理。他在德里学到宫廷阴谋,而且卷入了一场征服马尔代夫群岛的失败密谋。38
经历了前往斯里兰卡与印度东海岸的额外行程后,伊本·巴图塔在马拉巴尔海岸被分乘十二艘小船的海盗袭击,失去了他的财产。打从两百多年前亚伯拉罕·本·易尤的时代开始,海盗这回事一直没有什么改变。
但说到底,伊本·巴图塔还是活了下来。当地的商人与清真寺教长给了他衣服,他又重新起家。没过几天,他就再次陪在国王的身边,讲着故事,传递情报。公元1348年,伊本·巴图塔回到中东,这时的他已经迈入五十多岁的年纪了。他在大马士革停了下来,细细思量自己选择这种旅行生活的得失。从二十多年前离开大马士革的那一刻起,他就和自己在摩洛哥的家人断绝了联系,自此对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一无所知。在回到大马士革以前,他都不知道他的父亲于十五年前就已经过世了,而他在大马士革抛下的妻儿也都死了。伊本·巴图塔的习惯,就是短暂的婚姻与匆忙的离别,少说也抛下了七名妻子。他为了性欲买女奴,八成也在路上把她们给卖了。但在德里的时候,他似乎是真心为某个小女娃的死而悲恸;而这个女娃,则是他和妾所生的女儿。临到老时,他没有妻子,也没有孩子。
公元1348年,死亡也笼罩着伊本·巴图塔。同年,黑死病席卷欧洲,他也是头几个记录黑死病的人。
伊本·巴图塔从开罗走回摩洛哥的家乡。“对故乡的回忆牵引着我,而我对同胞与友人的喜欢、对故国的爱更是胜过一切。”41 他在公元1349年11月抵达非斯,这时他才知道自己的母亲已经在六个月前死于瘟疫。就像过去无数次的经验,伊本·巴图塔前往宫廷,找到国王。他接近摩洛哥王,讲起自己的宫廷、城市与王侯故事。这一回,国王资助了他,但要他写下自己的回忆。伊本·巴图塔最后写了本一千页的书,杂糅了故事与说教、贸易的机会与宫廷里的仪式,讲的则是他曾经历过的,以及他从中国到西班牙的城镇与宫廷里听来的一切。正是他对回忆录的撰写,占据了他的晚年。
在伊本·巴图塔的回忆录里,像他这样的人可以说俯拾皆是。他们身怀伊斯兰律法专业、宗教训练或是行政长才。这些人是整个伊斯兰世界里法律、宗教与学术的中流砥柱。他们从西班牙、突尼西亚与中亚出发,前往巴格达、德里,或是马拉巴尔海岸王国寻找工作机会。这些人绝不只是下层的小小官员。他们一如伊本·巴图塔,把新闻、八卦与各种故事从一个宫廷带到另一个宫廷。他们是关键的推动力,整个大亚洲世界的宫廷就是因为有他们,才会在象征、仪式与宫廷文化上渐渐变得相似。他们是变化的来源,就是要靠他们,一个国王—无论他是不是穆斯林—才能知道采纳这种共同的文化能为自己带来多少好处。

免责声明
本站部分内容来自于网络或者相关专家观点,本站发表仅供历史爱好者学习参考,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本文地址:/sjls/lgsz/270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