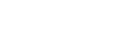对死者的祭奠比国家宗教普及更广,它被人们广泛接受,包括皇帝、贵族、豪强大族,甚至农民。然而,只有社会精英阶层才会留下作品,记录下他们的活动,将亡者埋入能够保存数个世纪的砖石坟墓。亲属系统中父系和家庭两者之间关系紧张,这使得它们的仪式在死者祭祀中的差别中彼此相关,这种差别存在于祖庙和墓葬之间:前者是宗族在仪式上得以被构建的场所;后者是夫妻合葬,伴随着模仿其生前生活的复制品或者形象,这一切重构了死后世界的家庭。
在公元前4世纪之后,一些墓葬采取了家宅或宫殿的外在形式,到了东汉以后,除了赤贫者之外,所有的墓葬都是家庭房屋的翻版。在战国晚期,视墓葬为房屋复制品的这种理念,不仅在实际生活中得到反应,而且还被表达为一种理论原则。于是,在儒家学者荀况的理论著作《荀子》一书中,有关仪式的章节如此写道:“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终始一也……故圹垅,其貌象室屋也;棺椁,其貌象版、盖、斯、象、拂也。”
以人世间的家庭为样板来修建墓葬的这种做法后来变得更加具体,更为流行。从西汉中期开始,人们通常会在崖壁上掘出洞穴来修建墓葬,而且把里面的空间分为不同的区域,分别是接待厅,通常用来放置尸身的房间,以及用于存放物品的耳室。在耳室前部和中部是木质建筑,带有瓦的屋顶。在厅的后部是石质建筑,上面装有一个石门。中等地主家庭的死者一般埋葬在用空心砖砌成的砖室墓中,是一个呈水平分布的圹穴。这种墓的布局通常也像一所房子,有一个山墙式的顶和一个大门形状的前壁。空心砖上通常都印有图案,一些墓壁上则有彩绘壁画,包括在墓顶上绘画太阳、月亮、星辰,以及代表四个方位的方位神兽,或者历史故事和文学故事。
不久以后,带有小砖砌成的穹隆顶的砖室墓逐渐取代了所有其他墓葬的型制。贵族、高级官员墓规制宏大,模仿着他们生前居住的精美住宅环境。壁画描绘着墓主人生前经历的场景,或者死者所向往的在死后世界的理想生活。
最后,到东汉时期,出现了一种新式的由分割成块、刻有图案的石块砌成的画像石墓。同样,墓葬的制式模仿着墓主人的生前生活,很多画像石描绘了墓主人的居家情景或者墓主人职业生涯中的事件。公元1世纪末,墓葬应该成为住宅居所的复制品这种观念如此流行,以至于王充提出了一个颇为夸张的问题:“宅与墓何别?”这意味着任何人都知道这二者之间没有什么不同。

图19 女人站在门道,欢迎死者到达阴曹地府,西王母和青鸟(使者)坐在一侧
尽管女性在父系社会中只是一个边缘化的角色,但是地下墓葬中的居宅很大程度上都以最后合葬在一起的夫妻之间的联系为主题。不但夫妻成双成对地“居住”在墓穴中,而且墓室画像中他们也坐在一起,还有一些亲密和感人的场景。一些场景描绘了主妇的女仆,她们通常是在纺织和采桑。其他的场景则显示出妇女游乐——舞蹈和宴乐——以及正在厨房中忙着准备宴席的工人。墓葬就和居宅一样,满是女性人物,她们扮演着主要角色。
在墓中绘画神灵是为了把墓葬变成一个宇宙,这些神灵也常常是女性。在几个墓中,一个女性神站在半掩开的大门口,欢迎着死者进入到死人的世界。(图19)汉墓中所绘的神灵更多的是西王母、伏羲和女娲。西王母站立在连接天地的昆仑之巅,她是墓主人们所仰慕的神仙世界的统治者。(图20)伏羲和女娲是一对神仙伴侣,他们的结合产生了世界,也因此为人世间的夫妻合葬提供了神灵界的模范。墓葬空间里这些女神所具有的重要性很值得一提,因为在文献中,她们都是级别较低的神。她们在文献中的地位和在墓葬中的地位是分离的,这个神灵世界反映出国家法定的父系制度和妇女操持家庭、产生非正式的影响这个社会事实之间存在着社会分离。

图20 西王母坐在虎(西)和龙(东)组成的宝座上,作为臣子的神兽围绕着她,包括九尾狐、金蟾以及信使青鸟。死去的夫妇坐在下面的角落
在西周时期的贵族墓中,随葬的青铜器和那些在古代庙坛中所使用的是一样的,尽管在级别稍低的墓葬中,它们经常被陶制品取而代之。到1000年后的东周中期,原来那些耗费极高的陪葬品有了廉价的替代品,即众所周知的“冥器”,而且已经成为随葬品的标准,除了那些最为精致的贵族墓葬。人间所用的祭器和随葬品之间的区别标志着这样一个早期阶段:建立在生者和死者共存基础之上的这个世界发生着戏剧性的变化。虽然周代早期的宗教仪式表明了生者和已经死去、一起参与祭享的亲属之间的联系,到了战国晚期,生者和死者之间的分离变成为葬礼的主要目的。
从战国晚期到汉代,周代礼器的组合被取代,墓中器物大多数是日用器(衣物、漆碗、盘、陶器、食物)或者是这些物品的模型,以及其他一些世俗生活的物品(房屋、谷仓、家畜、农具)。在这些复制品和人像中还有人类的形象,既有墓主人,还有仆人、戏子、厨子、农夫以及其他家庭生活的必须因素。这些人物为死者在墓中提供了一个充足和欢快的环境,它建立在对人世间的微观复制基础之上。荀子坚持认为墓中的这种“俑”——随葬品,尽管以生活中的物品为原型,但必须是与人世间的物品有明确不同的。
虽然这些礼仪文献通常不会讨论把死者和生者分离开来的理由,《礼记》中有一段文献却把这种做法的动机揭示了出来:“君临臣丧,以巫祝桃茢执戈,恶之也,所以异于生也。”在东汉墓葬文献中亡人都被描述为恶鬼,他们给生者带来疾病和不幸,除非确保他们被拘禁在坟墓。公元175年,一条律令被刻在一个镇墓陶瓶上,宣布“胥氏家冢中三曾五祖,皇□父母,离丘别墓。”它还用对偶句宣称了亡者和生者进行分离的必要性:
上天苍苍,地下茫茫。
死人归阴,生人归阳。
生人有里,死人有乡。
生属西长安,死属东太山。
生死异处,不得相妨。
乐无相念,苦无相思。
这个文献强调说,如果胥氏在阴曹地府犯有任何罪,那么随葬的一个蜡人将代替他服苦役,这样胥氏就永远不会再加害她活在世间的亲人了。它还强调,不允许较早去世的祖先迫使新近去世的人在他们的世界里担负刑罚性的劳役。这些段落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东汉时期信仰问题的最好证据,说明死者也要承受官僚政府所施加的审判和刑事劳役,而这个官僚政府正是以汉代政府为模板的。
苍山汉墓发现的“丧葬叙事”首先要求死者给他们后人带来财富和长寿,然后描述了在墓中刻画的人物的快乐,最后结尾时用一种冰冷而坚决的口吻,要求亡者和生者绝对的分离:
长就幽冥则决绝,
闭圹之后不复发。
尽管这种把死者视为一种威胁的主题只出现在某些特定区域和社会阶层的墓葬中,它们在汉代著作的故事中也有体现,故事讲述了怎样把死人骨头磨碎并投入毒汁里煮沸,以防死者进入生者的梦中危害他们。埋葬也是转移死者产生危害的方法之一,但是如果此法失败,这些故事中所描绘的更为剧烈的方法就会被使用。
现在还不能确定为什么很多中国人会视死者为一种威胁。战国时期和早期帝国时代的政治和礼仪著作都坚持要和死人保持距离,以防陷入混乱之中。除了诸如天和地之间的这类区分之外,生和死之间的区别是一个最基本的界线,一旦失去了它,世界将进入混乱的状态。死人一旦返回人间,就标志着这个界线的崩溃,这只能导致人间的大灾难。
战国晚期和早期帝国阶段,关于鬼魂讨论最多的是其作为复仇者的角色。在公元前4世纪的《左传》中,复仇的鬼魂有申生、伯有以及其他一些怨魂。他们进入人的梦境或站在人的面前,表达他们的怨恨,甚至会夺走人的性命。战国时期的哲学著作《墨子》努力证明鬼魂的存在,经常将其描述为怨魂。他们返回人世间,去惩罚那些在他们活着时得罪过他们的人。在西汉的《史记》中出现过关于怨魂的故事,而且它们成为中国历史和小说中经久不衰的话题。
除此之外,鬼魂出现在人世还带有以下目的:要求一个体面的葬礼,把尸体从遭到水淹的棺材中救出,或者提供其他方面的帮助,等等。最后,鬼魂会出现在病入膏肓的病人面前,把死者带走。战国时期和早期帝国时期,鬼魂通常在某方面出了问题时才会出现在人世间,他们会处罚生者,提出要求,或者把他们拉到阴曹地府。在一个运转正常的世界,死者和生者是严格分离的,因此,如果死者返回人间,就意味着有问题出现。
当死者被看作对生者的威胁时,以人的居宅模式来构建墓室之举就很好理解,这样做是为了努力给死者提供任何必备的东西,这样他们就会永远地留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但是,如果他们被困在一个单调的房屋内,就可能会不满意。一个完整的世界必定要有人物形象和复制品,这样才能使死者享受到可能的欢乐,而且满足于墓中的生活。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在秦始皇陵的顶部有一个苍穹的复制品,在地面上则是整个地理面貌。在描述富人和豪强大族的墓葬时,秦国哲学总集《吕氏春秋》说:“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
坟墓具有多重角色,作为居宅或世界,一个明确的例子在长沙马王堆被发现。棺中的一幅旗形帛画提供了一个宇宙的模型,地下是潮湿的阴曹地府,一个通过向墓中的棺木祭献的场景来表现的生灵的世界,以及一个标有日月星辰的星象图。在这个帛画下面,内棺形成一个完整、可供灵魂安居的世界。这个悬挂旗形帛画的内棺被一个外棺(椁)包围,它的装饰画包括操着武器和恶魔搏杀的长角的神灵,还有瑞兽和其他精灵。第三个棺木画面包括了一个崎岖的山顶,边上有龙、瑞兽和神仙——可能是昆仑山,这是一座位于世界最西端的神山,是西王母的领地。这些形象意味着坟墓或者棺椁也都能成为神仙的天堂。假设神仙们是和最西方的昆仑山或者和最东边(海上仙山)有关的天界神灵,那么这些形象就再次说明,这座墓葬神奇地包含着整个世界。
最后,棺椁被筑在墓穴中的木制框架环护。这个和住宅类似的阴间世界分为四个室,都有随葬品,营造了一个舒适的环境。北室仿照房屋的内室,有窗帘、地毯、餐饮器具、寝具、一幅漆屏风,以及穿戴整齐、正在表演乐器的塑像和赴会者。其他的几个室包含了贮藏有家用器具、食物和其他不计其数的代表着仆人的塑像。用坟墓的外部空间模仿一所房屋,而该“房屋”内的画像则表明墓葬是一个完整的宇宙,这种模式成为汉代墓葬艺术反复出现的主题。
类似马王堆出土的这种帛画在其他几座汉墓中也有发现,只是形式稍为简单一些。在鬼头山汉墓出土的棺木上,雕刻的装饰性图案包括有天门、伏羲和女娲、四方神、日月以及无数的仙人,还包括诸如谷仓这类建筑的复制品。在棺盖上反复出现了手举太阳的伏羲和手举月亮的女娲的主题形象,成为马王堆汉墓中通过神灵的弯曲的形体把天、地、人连为一体的宇宙形象的微缩本(图21)。天界是由日月来表示,人世间是由半人半神的形象来表示,地界则由他们的蛇形下体来表示。墓顶和墙上的形象包括日月、星辰、四方神、风神和雨神、西王母和仙人。西王母及其仙班的形象也出现在其他一些随葬品上面,比如青铜“摇钱树”。这些形象表明,仅仅只有居宅还不足以为死者提供一个完整的场所,而只有一个具备所有条件的完整世界才能让死者满意。这些形象还可以当作一张遨游八方的行程图。
阴曹地府有自己的统治秩序。刻在铅板上的墓主人“买地券”包括了墓地大小、购买日期、购买价格,以及为阴曹地府的官员提供的证人。这些官员包括天帝、司命、丘丞、延门佰史、地下二千石,以及多数墓都会有的墓伯。“买地券”规定,任何埋在墓葬里的物品都属于墓主人在阴曹地府中的财产,其他任何埋在那儿的尸体,都将变成他的仆人。其他“镇墓文”则召唤黄帝或其使者指挥天兵驱逐魔鬼的侵害。还有一些则乞求阴曹地府的官员,确保寿命计算不出差错,确保死者不会夭折或者不被误作其他地方的同姓名者而被勾去性命。在一座秦墓里还发现了一个故事,故事中官制杂乱,因为差错而受害的牺牲者最后复活了。类似的一个故事在汉代以后的世纪里,成为一个道德文学作品类型。

图21 伏羲和女娲拥抱着,蛇形躯体的下面部分缠绕在一起,他们擎举着日月
在汉代,尽管墓葬变成一个主要的宗教场所,豪族权贵仍然继续着坛庙祭享,一直到汉朝末期才发生变化。汉代文献和公元3世纪司马彪关于礼仪的专著记载了洛阳的两座古庙及其祭品。皇帝们在他们登基时都会前往这些庙坛,这里也会就牌匾的排列顺序举行辩论,文献记录了在这里表演的乐舞。公元190年,当都城被迫迁回长安时,祷告者都前往那里祭拜,他们都在蔡邕(133—192)的作品总集中被保留下来。
崔寔的《四民月令》残篇是一部关于地产经营和家庭事务管理的手册,该书指出,在公元2世纪,豪强大族就一直向祖庙和墓葬献祭:“正月之朔,是谓正日,及祀日。进酒降神毕,乃家室尊卑,无小无大,依次列坐先祖之前。”这种把展延家庭成员排陈在列祖列宗面前的方式,只可能在祖庙里举办,因为在祖庙里,列祖列宗的牌位都按顺序陈列着。和皇家庙祭一样,它们在一年中不时地举行。好几个部分章节都规定,墓祭在庙祭之后的第二天举行,这意味着后者在礼制上的优先性。和庙祭不同,墓祭还包括向非亲属提供祭献。
庙祭和墓祭之间的联系以及前者在礼仪上的优先性,在东汉末期司马彪关于帝国祭祀的记录中也有表达。这份3世纪的文献提到,东汉的第二位皇帝开了一个先例,皇帝不应该在他的墓地建造一个陵,而只在东汉开国皇帝庙里竖一个碑。于是墓祭只给予一些依据某些条件被挑选出来的妇女以及在成年之前就已经死亡、因而不能进入祖庙的皇帝。蔡邕在《独断》中规定:“少帝未逾年而崩,皆不入庙。”司马彪更认为这种排除的出现归因于以下事实:这些皇帝并没有真正地执政,因为他们的母亲在摄政。
庙坛仍旧是祖先崇拜最重要的地点,因为它是父系制最关键的仪式举办地点,而墓地则只是为个人或者家庭所保留。尽管妇女、儿童都不属于宗族真正意义上的成员,他们仍然能够继续享用皇家规格的墓祭,而庙祭既明确了宗族关系,又包括了政治权威。庙祭是召集真正的家庭成员——即宗族的男性成员——的机会,而墓祭则可能包括了更为广泛的社会阶层,包括政治监察官、师傅、朋友、乡老,或者远方的亲戚。墓葬的这种第二等地位在东汉时期开始出现的宗族墓地的组织方面也有所表现,因为它们都只是在墓葬的松散的呈现,不具备任何表达宗族组织的总体性结构。
由于庙祭在经典礼仪著作中就有叙述,而墓祭仪式最早不超过秦朝,东汉知识分子颂扬前者,视其为远古时代的特征;贬低后者,视其为战国晚期出现的一种发展,或者仅仅是秦始皇的革新。因此蔡邕这样写道:“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寝于墓侧,汉因而不改。”它沿用了大量东汉著作中的说法,这些著作把西汉和秦笼统地视之为一个礼制混乱的时期,同时标榜着他们身处的东汉,以为它恢复了正确的礼仪。在这种考量模式中,墓祭是秦朝的一种偏离正统的改革,而且被西汉给持久化了,而庙祭则根源于古典时代。
当代学者通常依据对假定的两种灵魂的信仰来分析汉代的墓祭礼仪:魂,是一种和“阳”相联系的“云”,以及和“阴”相联系的“魄”,这是一种混浊的“新月”魂。“魂”被认为将升入天堂,而“魄”则将永留阴曹地府。但是“魂”和“魄”的这种对立仅仅出现在《礼记》和《淮南子》这两个文献中,这是沿用了汉代学者把所有现象都和阴阳或五德终始联系起来的流行做法。而且后面这份文献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独特的道家宇宙观,和墓祭却没有任何关系。在和埋葬关系最紧密的书体文献——东汉石刻——中,“魂”和“魄”是被交互使用或合起来使用的。
对于战国和汉代作者而言,关键的问题不在于灵魂的性质,而在于合适的礼仪,特别是葬礼是应该精心准备、极尽奢华,还是朴素节俭、简单操办。早期儒家学者受到周代礼乐社会的影响,强调厚葬。在那个时代祖先崇拜是关键的宗教活动,也是对贵族身份的认定。与此相反,墨家学者抨击葬礼的奢侈之风,视其为浪费资源。由于社会精英倾注了大量资产用于葬礼,为了体面而竞争就意味着“匹夫贱人死者,殆竭家室”。
战国时期的哲学家荀子反驳说,多重棺椁、丰厚的随葬品、精致的装饰以及丧服制度都是通过葬礼维护等级制度,以此来捍卫社会秩序。《吕氏春秋》机警地回应说,厚葬属于弄巧成拙,因为它们招致了盗墓者:“今有人于此,为石铭置之垄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财物、宝器甚多,不可不,之必大富,世世乘车食肉。’人必相与笑之,以为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于此。”许多汉代的文献也都重复了这种观点,这证明它并没有受重视。
战国时期《庄子》中的传统论者认为,漂亮的棺材、昂贵的砖石墓墙使得尸体不能够和大地融为一体。然而,尸身不腐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马王堆出土的轪夫人墓,墓室做了细心的层层防护,用多层木炭和其他材料隔绝水分,使得该女尸发肤完好。另外,玉塞也会用来堵住身体上的窍孔,以此来防止人的精气从身体外泄。那些富有的人都设法采取这种步骤并形成一种逻辑认识,结果是把金镂玉衣覆盖全身。有大量考古发现证明了这点,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满城汉墓的玉衣,由超过2500枚玉片用金丝线缝合在一起。推翻王莽统治的赤眉农民起义军挖开了皇陵来寻找财宝:“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吕氏春秋》曾嘲讽地预测道,那些旨在确保死者获得永生而置于墓中的奇珍异宝,结果却导致他们的尸体被人随意弃置于地。
东汉的豪族把对死者的崇拜发展成为墓祠。在这个地方,参加仪式的不但包括家庭成员,而且还包括客户、助手或朋友。他们给那种通过教育、在政府任职的途径结成的社会网络一种宗教信仰的形式,这种网络逐渐把很多豪强大族联系在一起,共同对抗被宦官把持的朝廷。即便是在封闭墓门很久之后,墓祠的形象仍能被后人和亲友们瞻仰。这些形象向人们诉说着死者生前主张,并且把那些道德或者政治理念灌输给他的后人。山东武氏家族祠庙属于保留得最完好的墓祠之一,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完整、理想的微观世界。它的山墙尖顶部位描绘了世界边缘的神灵世界,墙上绘有男性的世界。后者的形象分为历史传说中的圣王和忠臣孝义,以及死者生活的场景,包括官员出行,格杀匪徒以及一幕舍身尽忠的场景。

免责声明
本站部分内容来自于网络或者相关专家观点,本站发表仅供历史爱好者学习参考,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本文地址:/zgls/qhjs/2785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