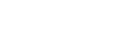◎商人的社会地位
在儒家重农主义者眼中,商人的社会地位是最低的。农民和手工艺者生产粮食、制作手工艺品,商人却不事生产,专以交换他人货物而得利。农民之所以值得称颂,是因为他们构建了社会的经济基础,并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养活广大民众。商人之所以社会地位低下,是因为他们的贸易行为不仅鼓励无妄的浪费,还会让农民偏离本业。在中国,重农主义者向来都努力维系着这种经济上的自给自足。然而,金钱却似乎妨碍了这种自足。
这种贬低商人的做法与社会现实是矛盾的。事实上,儒家正统蔑视商人,恰恰是因为商业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著书立说之时,正是强大的商人开始挑战既有的贵族秩序之际。因此,他对商业的轻蔑意在垂范未来,而非描述现实。换句话说,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并不意味着他们就真的为农民和手工业者不耻。后者也仅在名义上比前者优越而已。到帝制晚期,商人在国家专卖行业中起关键性作用时,即便普通商人,也被视为有价值的社会成员。然而,农业方面挥之不去的偏见,仍会不时对政府的商业政策产生不利影响。而文人们,当然也会继续空谈“士农工商”的旧秩序。
商人从街头小贩到巨贾,分类范围颇广。中国人通常将其分为三类:一般的贸易者(坐贾)、掮客(牙商)和富裕的寄销商(客商)。10世纪后,与这种功能上的分类随之而来的,还有贸易的发展。此时,修建运河促进全国市场的建立,对外贸易扩大,人们开始使用纸币和汇票,大城市也开始向旧的行政中心之外扩张。
<meta charset="UTF-8">◎商业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
明朝,商业继续发展。14世纪晚期,明朝建立者朱元璋再次统一天下后,中国又一次拥有全国性的市场。虽然高昂的运输费依旧妨碍主要商品的跨区交易,但此时已经出现私营部门为运送奢侈品开辟新的贸易路线。与此同时,诸如南北大运河(为运输粮税而建)之类的公共运输路线,不仅会运输粮税,也会运输私人货物。如果长江三角洲对山西原棉的需求量够大,往往就会有私人提供适当的运输工具。再举个例子:广东的商人想以他们的盐和铁交换北方的金银和布匹。结果,梅岭一线的挖土工、搬运工、赶牲者、护卫者纷纷成立各自的团体,保护精心设计的驿站系统和翻越福建群山的运货道路。
在明朝的统治下,运输困难得到缓解只是商业持续发展的原因之一。代代相传的土地和技艺对人们的束缚越来越弱,则是另一个原因。明朝的皇帝们在北方建起越来越多的皇家庄园,无意中迫使很多农民进入城市,成为一股不大不小的劳动力。此外,朝廷也会努力维持传承祖业的工匠团体,来鼓励能工巧匠的培养。这些团体的工人被迫贡献出一部分劳动力,为皇室修建宫殿、制作丝织艺品、烧制当时闻名于世的瓷器。晚明之际,朝廷放松了对这些木匠、泥瓦匠、织工和陶工的管制,让他们得以借助金钱,摆脱代代都为国家服务的状况,成为私人手工业者。
世袭劳役产业的松动和市场从属劳动力的解放,共同促成了赋税方式从实物向货币的转变。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认为,赋与役都用现银缴纳的“一条鞭法”税制改革,浇灌了16世纪晚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因为一旦可以用银两缴纳赋税,农民们就会种植更多经济作物。地主搬进城市,人们对手工艺品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商人们也积累起了商业资本。然而,也有观点认为,赋税货币化与其说是商业化的原因,不如说是其结果。因此,1550年至1650年间发生的其他几场社会经济变迁,应该受到更多重视。
例如,16世纪晚期,中等规模的集贸中心大大增加。像扬州和杭州这样的大城市,宋朝时仅有百分之十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明朝时,中国经历了另一波城市化浪潮。介于大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中型城市数量激增。定期交易的集镇(市)发展成为永久性的城(镇)。一个由乡村、城市郊区和城市之间的交易市场组成的网络覆盖了长江下游、开封和四川。这些营销中心鼓励新的消费习惯,给数百万从未经历过大城市奢华生活的人,带去了服饰潮流和戏曲娱乐活动。
地主也发现,这些新兴的中型市镇比乡村更适合居住。 如果我们相信当时人的主观印象,那就可以说,1550年至1650年间,土地所有权越来越集中,在有“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之说的长江下游地区,更是如此。士绅家庭利用他们享有的税收优惠特权,积累了成千上万亩分散的土地。来自这些土地的佃农租金,为富人们创造了搬入城市的条件。维持苏州宏伟的园林和繁荣的戏班花销巨大,这更增加了上层阶级对货币型租金,而非其他类型租金的需求。明朝统治的最后一个世纪里,虽然中国的白银出产量无法满足货币流通需求,但与日本和菲律宾的海外贸易带入了数以百万计的白银。 如此大的货币流通量不仅帮助支付了多种已经成熟的经济作物,还鼓励了本地待售产品的多样化。比如:苏州的铁器和精美的刺绣,浙江的毛笔、亚麻制品和蒲席。商人们把安徽的金属工具运到东南沿海,用销售获得的利润投资福建的假发,将其卖到江南地区。相应地,家庭手工业也日渐成熟起来。比如,13世纪时,只有城市里的工匠具备纺织精美锦缎的技艺,但到了16世纪,心灵手巧的农家孩子,也具备了相同的技艺。棉织品成为一种常规的手工艺品。明末时,中国四分之三的地区都出产棉布。缺乏土地种植棉花的农民,便从城里牙商那里购买原料,几乎完全依靠制造所得维持生活。对一份宗谱的研究 表明,许多这样的织工,后来都购进了几架织布机,再雇用几个工人,直到能维持起一个作坊规模的织布厂为止。丝织业也能维持农民家庭的生计。几代之后,他们的后人可能会逐渐成为小纺织厂的业主、商人,最后成为在诸如南京一类的主要城市拥有数间丝绸店的巨贾。
然而,“资本主义萌芽”并未发展成工业革命。棉纺织工艺尽管广泛传播,却从未在技术上有所进步。中国没能出现类似萨克森纺车或飞梭之类的发明,或许是原材料有限,而劳动力却过剩的缘故。这种情况下,人们也不会有什么动力发明节省劳力的装置,以生产出更多布匹。此外,棉纺织业是家庭手工业最常见的形式,每个家庭都能根据需要生产出大部分布匹。即便纺织业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长江下游地区,在纺织业中占主导地位的,依旧是个体农户。因此,整个棉纺织业的基础,就是庞大的、由市场机制协调的附属劳动力。而此处的市场机制,完全取决于不直接参与生产的商人。 织布的各个环节(轧棉、纺纱、染色、织造)并非在一个作坊里完成,而是倚赖一系列擅于处理复杂事务的中盘商、批发采购员、牙商和零售商,从商业角度将各个技术原始、相对分散的个体作坊联合起来完成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的需求比技术进步重要得多,所以熟练的经商手腕取代了有效管理。此外,棉花批发商远离生产第一线,所以基本不知道布匹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即便兼营批发的制造商,也因为中盘商的缘故,无法接触到实际的棉花生产过程。17世纪,苏州有七十位主要经销商以固定价格向劳工承包商购买布匹,而非自己雇用工匠织布。如此一来,商人们满足于按市场机制调整价格所带来的丰厚利润,根本没有提升技术的意识。因此,中国的商人或许能跻身世界一流商人的行列,却永远成不了大资本家。
<meta charset="UTF-8">◎商业贸易的不安全性
明清的商业成功,并没有自动为商人带来社会保障。财富可以买来政治影响力,却永远无法让官员俯首帖耳。商人们甚至连一个属于自己的辖区(一种如市政官或参赞管辖的,类似避难所的区域)也没有。16世纪迅速发展起来的城市,根本算不上自治市镇。大多数大型贸易中心,首先都被视为由督抚和州县官员进驻的行政中心。尽管汉字中有“城”(该字在中文里意为“墙”)这个词,中国的城市和乡村社会之间,却没有像其他文明一样,存在固定的疆界。大多数重要的城市中心与周边乡村并无明显界限。集市逐渐融入郊区,继而不断减少,最终与人口稠密的农田连为一体。区、县或省会的政府官署尽管都位于城墙以内,但那些城墙都是早期的边界,并未将17世纪和18世纪新拓展的城市景观包括在内。
在官员们眼中,这些城市的中心是不利于社会秩序的流氓无产阶级的温床。到了清代,城市里似乎随处可见秘密会社的恶棍、妓院老鸨、赌徒乃至市井无赖。他们聚众喧哗,象征着一种新的、与经济稳定的重农主义理念格格不入的商业文明。因此,当局煞费苦心地维持着对城市的控制权。城市行政依然归于中央官僚体系中,并未发展出市政机关之类的机构。直到20世纪初年,商人依然无法在其经商的城市获得任何形式的政治自治权。
他们也没有组织自治权。商会(行)最初为政府组建的手工业和贸易协会,起源于唐朝。“行”最初的意思是“排”或“街” ,被用来指精心规划的唐朝大都市中,政府将同业团体划归在一个城市区域的做法。比如,所有珠宝商都只能在“金匠街”开店,并接受政府指派的“行头”监管。行头不仅要监督质量、行会会员和业内价格,还要替政府征收行税。简而言之,贸易是一种必须向皇帝购买的特许权利。宋代的行会虽是一个更为自由的团体,却也从未完全摆脱官方控制工匠与商人的最初设定。虽然清朝也有其他类型的行会(比如中国中部和南部尤为盛行的“公所”和“会馆”),但帝制晚期的“行”,情况依然和之前一样。
18世纪,因为区域经济持续增长,会馆大为盛行。比如,北京的徽商便聚集起来,在首都建立起了会馆。这些会馆既可以作为酒馆或社交俱乐部,也可以作为能提供推荐信和有限商业信贷的商业合作协会。北京的这些会馆中,有些是由商人建立,用来接待进京赶考的士人举子的。因此,会馆不仅给商人提供了一个结交未来士绅的机会,也象征着商人终究需要依赖官方的保护。一个人在商场上爬得越高,他与官方的关系就显得越重要。虽然小商贾会尽力避免与官方接触,但牙商或客商发现,离开官方资助,他们的经营就难以为继。官员们常以控制贸易和价格为由,以贸易专卖权的许可为交换条件,向商人收取规费。向知府申请地方粮价控制权的粮食牙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向知府缴纳了银钱后,牙商便有权控制粮食批发商和将谷物带到市场上贩卖的农民们之间的贸易。除了用诡诈手段操控价格获利,牙商还可以从所有贸易中抽取一定比例的佣金。有时,牙商的剥削会大大超出农民的承受能力。但农民若试图脱离控制下的粮食交换体系,以建立他们的自由粮食市场,牙商就会向知府求援,请后者关闭农民的市场,支持其个人的垄断地位。
<meta charset="UTF-8">◎私人垄断
在其他社会,上述那些垄断情况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上,这里存在一种类似酒类销售许可的执照。只不过,这种执照在中国有属于它的特点,即:它与发证当局和领证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密切相关。牙商无法购买有法律保障的正式执照,只能以私人名义付费给个体官员。而那名官员被他人取代后,就需要洽谈新的合约。显然,优势在官府一方。既然这种执照一直都是暂时性的,那每次回收和再给予,都会使官员受利。反之,若官府售出的是永久性执照,该执照就很可能被一个牙商以极高的价格卖给另一个牙商,从而让得利的一方变成私人。因此,垄断协议非常适应市场环境,完美地预防了牙商滥用职权。如果牙商从农民那里勒索了太多钱财,后者的不满就会引起地方官的警觉。要知道,地方官对任何独家垄断商的容忍度都是极其有限的。他们总能收回执照,派给其他人。因此,从理论上来讲,牙商的过度剥削是可以受到控制的。实际上,这种制度却很容易遭到破坏。因为只要牙商给地方官多交点钱,后者就会牺牲农民的利益,与之勾结在一起。执照和腐败、行贿与受贿之间的界限,从未明晰到能够避免这类勾结。而且,儒家一贯的政治思想也更强调士大夫的道德操守,而非制度上的监督和平衡。
然而,帝国经济最发达的时候,也出现过可世袭的执照。18和19世纪期间,国家金融几乎被三个家族垄断。著名的山西票号就是这三个家族的产业。这些票号分别建立于18世纪初年,以全国性的汇兑为主要业务。因此,想把俸禄运回家乡,又怕遇到拦路抢劫的官员们,便成了他们最早的顾客。票号在收取了一定的费用后,就会派出保镖,护送官员的银两。随着声誉渐隆,票号逐渐开设了地方分号,发行能在其所有分号兑换现银的汇票。因为这些山西票号极有信誉,所以19世纪50年代起,朝廷也将钱存入这些分号,换取高额利息。作为回报,山西这三个家族向前途看好的应考者们发放优惠贷款。后者出任官职后,会充满感激地以存款或投资的方式,偿还票号的这份恩情。最终,这些山西票号便成了连通朝廷国库和地方藩库的半官方性的中转机构。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朝中支持山西票号的官员们绝不会允许其他任何票号在未得到三大家族许可的情况下,染指这项利润颇丰的生意。
与私营化更严重的部门相比,商贸和金融的公众化已经从多贸易商向集中化发展。涉足官僚资本主义的商人虽并未得到更多职务,但总体人数的持续下降,却让其个人财富相应增加。山西票号商人虽备受青睐,却无法集聚类似欧洲罗思柴尔德银行那样的财力。和欧洲的银行家们不同,他们既无法一步一步地从头积累资本,也没有能让他们成为帝国支柱的封邑或领地。对朝廷而言,他们只是一群可以利用的人,并非不可或缺。19世纪中期,山西票号商人资助如左宗棠等地方督抚大员时,是其最接近罗思柴尔德或伦巴第财团之际。19世纪90年代,当规模更大、实力更强的西方银行业随着帝国主义进入中国时,票号终究还是败下阵来。
<meta charset="UTF-8">◎盐业
官僚组织控制着高层金融的各个方面,这种国家垄断尤其体现在盐业上。从汉代起,朝廷就试图垄断盐的生产。盐是大众消费品,一旦征税,范围就将覆盖全民。然而,官僚体系不可能庞大到在每个零售点都派驻专人收税。因此,朝廷便控制了盐的生产。到清朝时,朝廷的盐业生产已经达到相当规模,在全国拥有十一个大盐田。最大的一个,是位于扬州附近——即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两淮盐田。该盐田包括三十个盐厂,六十七万两千名工人,每年向朝廷缴纳的赋税高达四百万两银子,占全国总税收的百分之六。
一千年前,两淮盐田这样的盐田,便已完全落入朝廷的掌控之中。唐朝的榷盐使都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正式官员,负责监督盐的生产、储存、运输和财务会计问题。从皇帝的立场来看,这样的官员管理似乎存在两个弊端:第一,它创造了一批仗着自己的专业水平,伙同僚属不服从中央管制的盐务专家。若这些盐使是经过传统训练成长起来的文学通才,就更是如此。第二,它为地方官员提供了一个新的且独立于中央之外的收入来源。如此一来,便为军事割据势力奠定了经济基础。瓜分了唐帝国的地方军头们,便严重依赖本地榷盐使的忠诚和创收能力。
然而,到了清朝,盐业的组织模式发生改变,将高层官僚监管与商人管理盐业生产和分配的方式合为一体。盐运使都从皇帝的亲信(即由旗人或对皇帝忠心不贰的包衣家奴组成的内务府)中选任,必须要与皇帝和户部共同承担制定政策的责任。事实上,他们的职责之一,就是把盐税直接送进皇帝的大内财库。即便这么做会导致无法完成户部分摊的税收额,也在所不惜。
大部分时间里,盐运使的角色都并无变化,相对稳定,但复杂的商户管理,却在帝制晚期发生了巨大变化。盐业生产交到了漕户手中。后者在盐田将盐转手给盐商(也称“内商”或“场商”)。然后,盐商奉盐政衙门之命把盐运到扬州,在那里装船、课税后,交给负责运输的水商,再由水商分发给零售业者。从该制度在14世纪首次施行起,水商要是无法出示盐引以证明其已经帮朝廷筹备过边疆军事物资,就无法运盐。这种旨在让盐商充作明政府军事后勤的复杂制度,很快便崩溃了。到16世纪,山西和安徽的水商不仅能直接进入盐田,还能直接从盐运使手中购买盐引。
17世纪,水商在盐业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不可或缺。他们购买盐引的费用,也成了朝廷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明朝军费因为满洲人入侵而大增时,朝廷曾试图强迫商人提前购买未来二至三年的盐引许可,来增加额外收入。商人们通过拒绝购买这些预售的盐引,来表达自己无声的抗议。除非盐务官员答应扩大运输额度,并让他们以现有盐引运输,他们才会妥协。其中一些更具投机野心的盐商,甚至趁机买下同行的旧盐引,以求增值获利。当然,盐务官员可以裁定旧的盐引许可无效,借此打破盐商的专卖局面。然而,官员们发现,盐业贸易过于庞大,只有眼前这些商人,才有足够资本预购盐引。因此,在盐务官员的请求下,朝廷于1617年做出重大让步。任何购买新盐引的人,都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获取永久性的运输选择权。对那二十四家水商来说,朝廷的这次妥协,无异于一场巨大的胜利。很快,他们便将这种选择权转换成家传许可——“根窝” 。18世纪,这项特权为他们的后代积聚起了巨额财富。
盐田里场商的数量越来越少,他们的个人财富却越来越多。到18世纪,仅三十名场商,就完全控制了整个两淮盐场。这种集中的趋势也反映出了朝廷的认可:只有最富有的商人,才能承担起囤盐一年的资本风险。存盐变质的可能性一直都存在,因此,盐务官员必须确定盐商们有足够现银,可以挺过足以让小商贩倾家荡产的仓储损坏。因此,集中化的经济趋势,就势必牵涉到经济规模。在规模如此巨大的贸易活动中,与大量从事地方市场交易的商人相比,的确只有少部分人具备经营全国性市场的能力。因此,经营权就逐渐落入了少数人手中。
期望更有效地规范贸易行为的官员们,也急需实现商业集中化。朝廷甚至鼓励少数大商人垄断专营权,来达到遏制私盐销售和走私的目的。因此,资深商人便成了小商人的担保人。没有前者的允许,后者就无法涉足盐业。至少从理论上来讲,这种垄断行为起到了稳定盐价的作用。因为,它较少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综上所述,引领行业的商人数量,一直都在持续下降。到1730年,所有水商与场商都被纳入五位首席盐商(即“总商”)的庇护之下。总商同意承担行业内的主要风险,以换取最大的利润。
利润如此显而易见,当然会有人期望总商们有所表示。总利润中有一部分自动拨作馈赠、酬酢及贿赂历任监督盐场的官员之用。皇帝每逢节日和寿诞,也能直接收到捐供。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费用是总商获得世袭专营许可的例行回报。但这种变幻莫测的各种非正规规费,促使贪官寻找各种借口(如走私猖獗、贩售私盐等)向盐商及其担保人敲诈更多钱财。因此,官僚资本主义在获得巨大利润的同时,也承担着高风险。整个18世纪,盐业利润高达二点五亿两银子,提供给盐商的可用资本为八千万两。
要维持盐业生产与销售的稳定,资本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有了上述的可用资产,商人们通常都不会遭遇彻底的经济崩溃。一名典型的盐运使,通常都出生于内务府。他花费了大量银子上下打点,才从宫中得到这个自己垂涎已久的职位。同样,皇帝也期待盐运使知恩图报。因此,他上任后若没有立刻将贵重礼品送达御前,皇帝就可能以渎职的名义惩罚盐运使。考虑到这些财务上的难关,每任盐运使都会在自己短暂的任期内,极力榨取更多钱财。与此同时,他也知道如果将商人逼至破产、甚至被迫暂时缩减交易的境地,自己就无法完成内务府摊派的税额。清朝的皇帝经常忽视盐运使无法完成规定税额的过失,却无法容忍自己的私库收入减少。为了保住项上人头,历任盐运使无不小心翼翼,唯恐激起商人过多的愤懑。因此,官员与商业利益的密切关系,就是官僚资本主义的核心。这个局外人眼中或许充斥着任意征税和随意贿赂的腐败系统,其实是受不成文的规则和经济现状制约的,实际上运作良好、规则微妙的非正式官-商机制 。
<meta charset="UTF-8">◎商人追求士绅文化
尽管次数不多,盐商还是会利用自己庞大的经济资源,来反抗督管他们的盐务官员。不过,即便如此,他们依然被这些上层的社会价值牢牢地束缚着。商人接受官绅管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也有可能进入精英阶层。有机会购买低阶功名,科考的开放,加上出身低微的人再也不必面对无法逾越的贵族秩序,像郑氏家族一样的总商家族,就有一半的男丁可以获得官方士绅的地位。这种富有的大户请得起全国最好的塾师来教导族中子弟,帮助他们应考朝廷为这些家族特意保留名额的恩科考试 。商人既然可以如此轻易地进入精英阶层,他们就没有推翻儒家等级制度的动力,也没有联合其他资产阶级同业,共同提高其社会地位的志向。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资产阶级的一员。因为可以轻易地以个人名义进入他们梦寐以求的士绅阶层,所以这些商人既缺乏从意识形态上证明自己的动机,更无法得到启发,构想出一种类似加尔文主义的中国式道德规范。
商人也没能养成自成一格的举止礼仪或生活方式。他们一掷千金、大肆效仿士绅的举止,放弃了更有成效的投资,转而重申文人高雅文化的霸权地位。例如,当时一个特立独行的“盐呆子” ,就曾在设计精巧的玩具、太湖石 和珍奇的宠物上大肆挥霍。然而,他的这些行为,依然只是在以一种夸大的方式,扭曲地理解士绅风尚。所有此类挥霍行为中,盐商出身的马氏家族不仅主持了18世纪最著名的文化沙龙,资助着当时许多著名的艺术家,还拥有一个私人藏书楼,里面存放着许多让乾隆皇帝都艳羡不已的珍本。他们对传统士绅风格的发展,与日本大阪的米商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几乎与中国盐商处于同一时期的米商,都很享受他们独特的都市文化。歌舞伎、傀儡戏、井原西鹤小说中的“浮世绘”和安藤广重的浮世绘本,都是多愁善感、充满肉欲的,与日本正统武士文化里严苛的价值观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在18世纪的扬州,旧时的精英文化形态几乎没有任何改变。诚然,中国最伟大的白话小说就诞生在这个时代。但《红楼梦》里讲述的,仍是内务府出身的盐运使家族,而非表面上归其管辖的那些商人。
扬州的盐商请人绘制的一些古怪画作,的确能反映新的审美观。但仅高其佩的指画和金农虬奇的山水画,或许并不能代表资产阶级已经把注意力转到文化创新层面。上述画作旨在传达一种文人墨客故意为之、与旧日宫廷职业画师那种精雕细琢之风背道而驰、不带匠气的画风。只有经过良好的教育,熟练掌握了宋、元、明绘画笔法和书法技巧的人,才能明了文人山水画里这种标新立异、匠心独具的变体画法。相比圆滑地迎合新贵的审美情趣,这些文人更在意浑然天成的古拙之意。事实上,这些文人绘画的受众,几乎都是与他们自身类似的、有能力欣赏多重意象的唐宋书画主题的人。用一位艺术史学者的话来说,这种极端矫饰的鉴赏能力是基于:
现在与过去之间,个人感受力的极限与超出其个人理解范围的文化传承之间,进行的一场精心对话。
“过去”就像一副重担,压在“现在”的肩上。18世纪,行径古怪的文人们虽作风狂放,却只是通过颠覆传统来表达自己的创新性。换句话说,他们找不到一种新的、属于自己的绘画语言。也许,他们愚钝粗鄙的赞助者会通过将其限制在高雅文化的幻影中,来阻碍他们的创新。毕竟,培养自己迎合画家品味的,是身为资产阶级的买家。然而,扬州艺术家们取得文化优越感付出的代价,仍旧是不断地重复。所以,他们的画作无论多么有独创性,也跳不出宋、元、明的绘画主题。
同样的局限性也体现在了诗歌上。18世纪伟大的田园派诗人袁枚也和同时代的人一样,接受“盐呆子”的赞助。他感受到了传统的重担,极力抨击盲目模仿中古诗风的人。他不拘一格的诗句虽然感动了读者,却依然无法跳出唐宋的诗歌格律。然而,无论袁枚的诗句多么独特、大胆,他选择的艺术载体,依然是读者熟悉的古典语言。
中华文明最恢宏的文化遗产 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拙劣地编进了乾隆皇帝那三万六千卷的《四库全书》中。《四库全书》是套包括了过去所有重要典籍的文选。为此,盐商藏书楼中的珍本都被征用、送往北京。无数德高望重的学者不遗余力地编纂大量总目纲要,剔除非正统的作品,然后把定版抄录副本。袁枚虽然主张浪漫的个人主义,反对因袭陈规,但也渴望加入这一编纂工程。他的一个朋友受命加入《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时,袁写道(显然,他的话中并不含讽刺意味):
我似乎还是无法避免地被列入了无知的行列。我所闻有限,治学不严。转头回望都城,只能徒然一声长叹。要是能加入你们,助你完成这项艰苦的事业,该有多好!既然如此,你或许可以列出一些书名随信寄来,我应该能提供一些粗浅的见解。如此一来,我或许才不会觉得,自己枉读了一番圣贤之书。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所有文化的抱负归根结底不仅都与政治有关,还专注于权力顶峰的那张宝座。正如商人,无论多么富有,都会渴望跻身士绅之列。文人亦是如此,无论多么锐意创新,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在京城为皇帝效命。
<meta charset="UTF-8">
免责声明
本站部分内容来自于网络或者相关专家观点,本站发表仅供历史爱好者学习参考,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本文地址:/ysxl/lsxh/27027.html